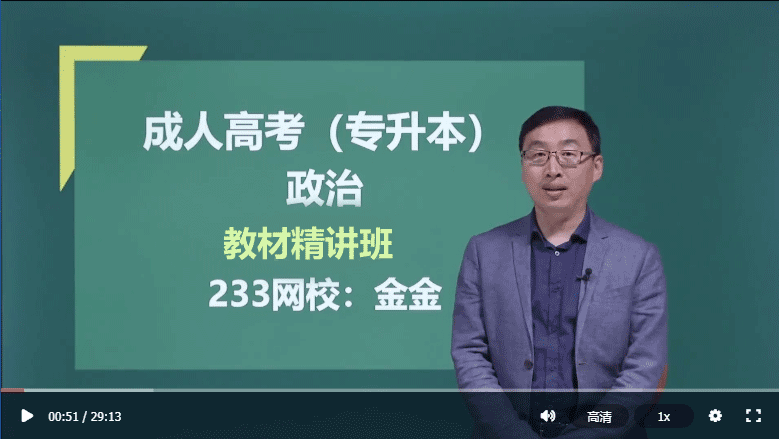一个月来,大太阳一直朝着田野喷下灼人的火焰。在这火雨的浇灌下,生命的花朵盛开,欣欣向荣。绿油油的大地一眼望不到边。蓝湛湛的天空上没有一丝云。诺曼底人的农庄分散在平原上,被又高又细的山毛榉围着,远远望去,好似一片一片的小树林。走到跟前,推开虫蛀的栅栏门,却又叫人以为是一座大花园,因为那些像农民一样瘦骨嶙峋的老苹果树都开了花。黑黝黝的老树干,歪歪扭扭,成行地排列在院子里,向着晴空撑开它们的圆顶,白的白,红的红,光彩夺目。苹果花的清香,敞开的牲口棚里散发出的浓烈气味,还有厩肥堆发酵冒出来的热气掺混在一起。厩肥堆上歇满了母鸡。
中午,这一家子:父亲、母亲、四个孩子、两个女雇工和三个男雇工,正在门前那棵梨树阴下吃饭。他们很少说话,喝过浓汤以后,又揭开了盛满肥肉烧土豆的盆子。
不时有一个女雇工站起来,拎着罐子到地窖里去装苹果酒。
男主人四十来岁,高个儿,他打量着屋边一株还没有长出叶子的葡萄。葡萄藤像蛇一样沿着百叶窗下的墙壁,蜿蜒伸展。
最后他说:“爹爹的这株葡萄今年发芽发得早。说不定要结了。”
女主人也转过头来看看,不过没有开口。
这株葡萄栽的地方正好是老爹被枪杀的地方。
事情发生在一八七。年的战争中。普鲁士人占领了整个地区。费德尔布将军率领着北方部队还在抵抗。
普军的参谋部当时就设在这个农庄里。农庄主人米龙老爹,名字叫皮埃尔,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农。他接待他们,并且尽力把他们安置好。
一个月来,德军的先头部队一直留在村里侦察情况。法国军队离着有十法里,不见有一点动静。可是。每天夜里都有普鲁士骑兵失踪。
派出去执行巡逻任务的侦察兵,只要是两三人一组出去,就从来没有回来过。
到了早上,在田野里,院子旁边或者沟里找到他们的尸体。他们的马也被割断喉咙,倒在大路上。
这些暗杀事件看来像是同一伙人干的,但是凶手始终没法查出。
普鲁士人在当地实行了恐怖的报复政策,许多农民仅仅根据简单的告发就被枪杀;许多妇女被监禁。他们还想用恐吓手段从孩子嘴里套出话来。结果还是什么情况也没有发现。
谁知一天早上,有人看见米龙老爹躺在他的马厩里,脸上有一道刀伤。
在离农庄三公里外的地方找到了两个肚子被戳穿的骑兵。其中一个手上还握着沾满血迹的武器,可见他曾经搏斗过,进行过自卫。
军事法庭立刻在农庄门口的露天地里开庭。老头儿被带上来。
他那年六十八岁,个子瘦小,背略微有点驼,两只大手好像一对蟹钳。失去光泽的头发,稀稀落落,而且软得像小鸭的绒毛,到处露出头皮。脖子上的皮肤是褐色的,布满皱纹,露出一根根粗筋;这些粗筋从颚骨底下钻进去,然后又在两鬓现出来。他在当地被认为是一个吝啬而又难弄的人。
他们叫他立在一张从厨房里搬出来的桌子前面,四个士兵围着他。五位军官和上校坐在他的对面。
上校用法国话问:
“米龙老爹,自从我们来到这里,一直是对你非常满意。你一向对我们很殷勤,甚至可以说,非常关切。但是,今天有一桩重大的案件牵连到你,因此必须弄弄清楚。你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这个农民一句也没有回答。
上校又说:
“米龙老爹,你不说话就证明你有罪。不过,我要你回答我,听见了吗?今天早上在十字架附近找到的那两个骑兵,你知道是谁杀的吗?”
老人毫不含糊地回答:
“是我杀的。”
上校吃了一惊.他盯着犯人看,沉默了一会儿。米龙老爹一直保持着平静的态度,仿佛是在跟本堂神父说话,低垂着眼帘,脸上带着庄稼人的那股子傻气。仅仅从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慌乱,那就是他在一下一下虽然很使劲地咽口水,就像他的嗓子完全被卡住了似的。
老头的全家:他的儿子让,儿媳妇,还有两个孙子,惊慌失措地站在他背后十步以外。上校又问:
“一个月来,每天早上在野外找到的我们军队里的那些侦察兵,你也知道是谁杀的吗?
老人仍旧呆头呆脑,毫无表情地回答:
“是我杀的。”
“全都是你杀的吗?”
“不错,全都是我杀的。”“你一个人杀的?”
“我一个人杀的。”
“告诉我,你是怎样干的?”
这一下,他有点紧张了;要他讲很多的话,显然使他感到为难。他吭吭哧哧地说:“我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碰上就怎么干。”
上校说:
“我通知你,你非把一切经过告诉我不可。所以你最好还是赶快拿定主意。你是怎样开的头?”
老人朝他的家里人不安地看了一眼,他们在他背后注意地听着。他又迟疑了一会儿,这才突然下了决心。
“有天晚上我回家,大约就是你们来到的第二天,十点左右。你,还有你那些当兵的,你们拿走了我值五十多埃居的草料,还有一头母牛和两只绵羊。我对自己说:‘好,让他们拿吧,我都得叫他们赔出来。’我心里另外还有别的委屈,等一会我再告诉你。先说那天晚上,我看见你手下的一个骑兵在我粮仓后面的沟沿上抽烟斗。我连忙去把我的镰刀摘下来,悄悄摸到他背后,他一点也没有听见。我就像割麦子似的,一镰刀,就这么一镰刀,把他的脑袋削下来了。他甚至连喊一声哎哟都没来得及。你只要到池塘里去寻一寻,就可以发现他跟一块顶栅栏门用的石头一起装在一只煤口袋里。“我有我的主意。我把他全身的衣物,从靴子一直到便帽都扒下来。我把这些东西藏在院子后面,马丹家那片树林中的石灰窑里。”
老头儿不说下去了。军官们惊讶地互相望着。审问接着又重新开始;以下就是他们问出来的。他一旦动手杀了那个骑兵以后,就念念不忘,一直想着:“杀普鲁士人!”他恨他们,他对他们怀着一个既贪财而又爱国的农民才会有的那种阴狠的、强烈的仇恨。正像他自己说的,他有他的主意。他等了几天。
他对战胜者是那么谦恭,既殷勤而又驯服,所以他们让他自由来去,随意进出。每天晚上他都看见有传令兵出发。他跟士兵们经常接触,学会了几句必要的德国话。一天夜里,他听到骑兵们前往的那个村庄的名字以后,就出去了。
他走出院子,溜进树林,到了石灰窑就连忙钻进那条长坑道。他在地上找到那个死人的衣服,穿在身上。
然后,他在田野里转来转去,一会儿爬,一会儿躲躲闪闪地沿着斜坡走,只要有一点响声就注意听,像违禁偷猎的人那样紧张不安。
他认为时间到了,就来到大路边上,藏在荆棘丛里,继续等着。将近半夜十二点,硬土路面上终于响起了嗒嗒的马蹄声。他把耳朵贴在地面上,听准了只有一个骑兵过来,就做好准备。
那个骑兵带着紧急公文,骑着马疾驰而来。一路上他耳目并用,小心提防。米龙老爹等他来到十步远的地方,连忙爬到路当中,叫喊:“Hilfe!Hilfe!(救命!救命!)”骑兵勒住马一看,认出是一个落马的德国人,以为他受了伤,于是跳下马,毫不怀疑地走过来。正当他朝陌生人俯下身子的时候,那柄弯弯的长马刀就戳进了他的腹部。他倒下去,仅仅抖动了几下,就立刻断气了。
接着,这个诺曼底人怀着老农民才有的那种不动声色的快活心情站起来。为了取乐,他又把死人的喉咙割断;然后才拖到沟边扔下去。
马静静地等候着它的主人。米龙老爹跨上马鞍,一溜烟地朝平原上奔去。
一个钟头以后,他又看见两个并排返回营地去的骑兵。他笔直地朝他们跑去,嘴里又叫着:“Hilfe!Hilfe!”普鲁士人认出了军服,让他过来,丝毫没有起疑心。老头儿像颗炮弹在他们中间一穿而过,用马刀和手枪同时把他们俩都撂倒了。
他把两匹马也宰了,因为那是德国人的马!然后悄悄回到石灰窑,把一匹马藏到阴暗的坑道里。他脱掉军服,换上自己的破衣裳,回到床上,一觉睡到天亮。
他等候侦查结束,一连四天没有出门。但是到第五天,他又出去了,用同样的计策杀死了两个士兵。从此以后他一直没有歇过手。每天夜里,他这个幽灵般的骑兵,这个专以杀人为目标的猎人,都要披星戴月在荒凉的田野里奔驰。他忽东忽西,到处寻找机会,有时在这儿撂倒几个普鲁士人,有时在撂倒几个。任务完成以后,这个老骑兵就撇下倒在大路上的尸体,回到石灰窑里把马和军服藏好。
到了中午,他从容不迫地拎着燕麦和水去喂留在坑道里的坐骑。他把它喂得饱饱的,因为他需要它干的是一桩很重的活儿呢。
但是,头天晚上,遭到这个老农民袭击的人中间,有一个有了防备,在他脸上砍了一刀。
不过,他还是把那两个人都杀死了。他还能够回到石灰窑,把马藏好,换上破旧的衣裳,可是在回家的路上,他感到身子发软,勉勉强强走到马厩,就再没有气力往家里走了。
他被人发现时;正躺在干草上,浑身是血……
他讲完以后,突然抬起头,自豪地望着普鲁士军官。
上校捻着小胡子,问他: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没有了。账已经算清,不多不少,我一共杀了十六个。”
“你知道你有死罪吗?”
“我又没有向你讨饶。”
“你当过兵吗?”
“当过。我从前打过仗。再说,我那个跟拿破仑一世皇帝当兵的爸爸,就是你们打死的。上个月你们又在挨夫勒附近打死了我的小儿子弗朗索瓦。我欠你们的债已经还清。现在咱们是谁也不欠谁的。”
军官们面面相觑。老人接着说下去:“八个是为我爸爸还的,八个是为我儿子还的。咱们谁也不欠谁的了。我呀,我可不是成心要跟
你们过不去!我根本不认识你们!就连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可是你们来到我的家里,就跟在你们自己家里一样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我已经在那些人身上报了仇。我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老人挺直僵硬的腰板,像一位谦逊的英雄那样把双手交叉在胸前。
普鲁士人低声交谈了很久。有一个上尉也是上个月才失掉自己的孩子,他为这个行为高尚的穷苦人辩护。
后来上校站起来,走到米龙老爹跟前,压低嗓音说:
“听我说,老头儿,也许还有一个办法救你的性命,只要……”
可是老人家根本不听。微风吹拂着他脑袋上绒毛般的稀发,他两眼逼视着打胜仗的军官,眉头一皱,那张带着刀伤的瘦脸扭歪了,表情十分可怕。接着他挺起胸膛,使出全身力气朝普鲁士人脸上吐了一口唾沫。
上校气疯了,他刚举起手,老人又朝他脸上吐了一口。
军官们都立了起来,同时大声地发布命令。
不到一分钟,这个仍旧十分平静的老人就被推到墙根处决了。他的儿子让、儿媳妇和两个孙子惊慌失措地望着,他在临死前还朝着他们微笑呢。
2015年成考《大学语文》米龙老爹考点及试题
相关阅读
-
2015年成考《大学语文》长亭送别考点及试题
-
2015年成考《大学语文》日出(节选)考点及试题
-
2015年成考《大学语文》断魂枪考点及试题
-
2015年成考《大学语文》苦恼考点及试题
-
2015年成考《大学语文》麦琪的礼物考点及试题
-
2015年成人高考大学语文戏剧考点及试题汇总
-
2015年成考《大学语文》风波考点及试题
-
2015年成考《大学语文》宝玉挨打考点及试题
-
2015年成考《大学语文》天净沙•秋思考点及试题
-
2015年成考《大学语文》前赤壁赋考点及试题
-
2015年成考《大学语文》水龙吟考点及试题
-
2015年成考《大学语文》声声慢考点及试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