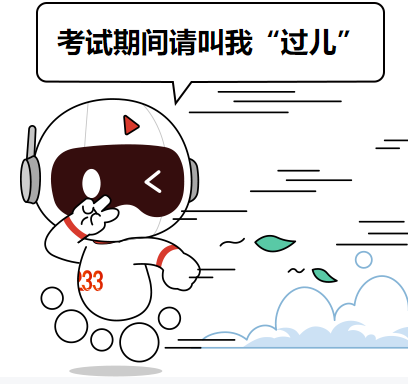|
财政年度 |
法币增发额 |
公债收入 |
财政赤字 |
法币增发额、借债收入占财政赤字的百分比 | |
|
1937-1938 |
3 |
11.56 |
15.32 |
19.6 |
75.5 |
|
1938下半年 |
6 |
3.18 |
8.72 |
68.8 |
36.5 |
|
小计 |
9 |
14.47 |
24.04 |
37.4 |
60.2 |
|
1939 |
20 |
3.25 |
20.82 |
96.1 |
15.6 |
|
1940 |
36 |
2.08 |
39.71 |
90.6 |
5.2 |
|
1941 |
72 |
23.72 |
88.19 |
81.6 |
26.9 |
|
1942 |
193 |
9.56 |
192.42 |
100.3 |
5.0 |
|
1943 |
410 |
38.71 |
422.99 |
96.9 |
9.2 |
|
1944 |
1141 |
16.47 |
1354.73 |
84.2 |
1.2 |
|
小计 |
1872 |
93.79 |
2118.86 |
88.3 |
4.4 |
[1][5]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页;1943年的百分比经重新计算,与该书中的数据略有不同。
[2][6] 从1939年起,国民政府的财政年度由“跨年制”(当年7月—次年6月)改为“历年制”(当年1—12月),所以1938财政年度只包括下半年。
如上所述,孔祥熙在抗战中后期的确实行了以发钞为核心的战时财政政策。这就背弃了他在理论上所主张实行的以借债为核心,以增税、发钞为补充的战时财政政策。而他之所以背弃自己的理论,则是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是战争的特殊需要和增税、借债的低效益迫使他这样做。战争具有变幻莫测、消耗巨大的特性。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战时财政的主持者必须想方设法迅速筹得巨款以确保战费需要。而从理论上说,发钞是战时最易于奏效的筹款方法,因为与增税、借债等常用筹款方法相比,它具有手续简便、成本极低、单靠国家强制力就能在无形中把大量财富迅速集中到政府手里的优点,即便是“最弱而无能的政府亦能实行之”。[1][1]不过,发钞过度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所以有识之士在筹划战时财政时,既主张用它来筹集战费,也强调适度原则,反对过量发行。孔祥熙也强调这一点。他说:“为求收入迅速,以战时需要计”,“亦必利用”发钞办法来筹款,但须“毋使过量,以防流弊”。[2][2]话虽如此,可实际上发钞的“度”是难以把握的。因为战时生产往往较平时萎缩,结果导致物价飞涨,进而带动战费开支的激增。此时,如果财政当局不能有效利用借债、增税办法回收流通中因生产萎缩而相对过剩的钞票,然后用这些钞票来应付战费开支的激增,那就只好依靠增发钞票来供应战费开支了,于是就会不自觉地超出发钞的“度”而走上滥发钞票的绝路。孔祥熙在抗战中后期就因为类似的原因而走上了滥发钞票的绝路。一方面,抗战期间增税、借债的效益极差,前者仅能支付政府财政总支出的6%,后者仅能弥补政府财政赤字总额的5%[3][3];另一方面,战费开支又急如星火,且数额巨大,动辄占每年财政支出的60-70%[4][4]。在这种情况下,孔氏作为财政部长,虽然明知发钞过度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但为了使国民政府能够坚持抗战,他只得走上滥发钞票的绝路。
二是他对发行战时公债产生了畏难情绪。1939年,面对抗战初期向人民直接发行公债“成绩迄未显著”困难局面,他不是知难而进,想方设法改善其成绩,而是哀叹说:“此后虽仍拟积极劝募(公债)”,但“将来有无更好成绩,殊难预知”。[5][5]在这种畏难情绪的作用下,他过早地放弃了向人民直接发行公债的努力,轻率决定“仍将以押借办法为主”发行公债,也就是把大多数公债抵押给国家银行,再由国家银行借款给政府。而用向国家银行押借的办法发行公债,势必走上滥发钞票的道路。因为国家银行既无权强迫人民认购公债,也无法一直以人民的存款来满足政府的借款需要,就只得以公债为准备金增发钞票,再借给政府。这样,发行公债便和发行钞票无异,等于是变相的通货膨胀,即以发行公债为名,行发行钞票之实。于是,发行公债愈多,发行钞票也愈多。久而久之,原来实行的以借债为核心的战时财政政策也就变成了以发钞为核心的战时财政政策。
三是他一度用一种荒谬理论来指导法币的发行。他在1940至1941年间曾反复贩卖如下理论:“迨战事发动以后,抗战建国同时并进,通货之需要因之更形殷切,发行数额自有相当之增加。但发行数额是否逾量,不在乎数目之多少,而全以是否适合于社会之需要及已否超过饱和点为定。若依此衡量我国之现在发行数量,不但未超过饱和点,且反在饱和点以下。”[6][1]这是一种无视恶性通货膨胀的存在而企图为滥发钞票政策辩护的荒谬理论。1940至1941年间,大后方已经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因为当时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的重要标志——物价上涨速度超过法币的增发速度。如以1937年6月的物价和法币发行数为1,则1939年12月重庆批发物价指数为1.77,仍低于此时的法币发行指数3.04,但到1940年8月时,前者增至4.94,已超过后者的4.72,这表明恶性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到1940年12月时,前者增至10.94,后者仅为5.58,1年后,前者增至28.48,后者仅为10.71[7][2],恶性通货膨胀已愈演愈烈。而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钞票发行量虽然增加,但其所代表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总量反而降低,所以不会超过“饱和点”(商品流通和劳务实际需要的货币量);钞票发行量越多,其所代表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总量越低,也就永远不会超过“饱和点”。这就是上述理论的真意所在。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法币的发行量必然漫无节制。
--------------------------------------------------------------------------------
[1][1] 丁洪范:《非常时期财政应否以通货税为出路》,《大公报》1936年7月1日第11版。
[2][2] 孔祥熙:《战时财政与金融》,《演讲集》,第240页。
[3][3]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第98页。
[4][4]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102页。
[5][5] 孔祥熙:《最近财政实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第357页。
[6][1]孔祥熙:《一年来之战时财政》、《抗战三年来之财政与金融》,《三十年来之我国财政》,《大公报》,1940年元旦第3版、1940年7月7日第4版、1941年1月1日第8版;《今后财政之展望》、《抗战四年来之财政与金融》,《演讲集》,第282、318页。
[7][2] 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第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