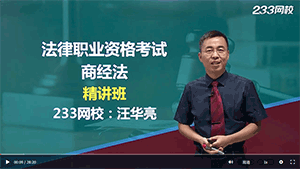三 死刑存留论之基础
(一) 曲折的死刑论
决定死刑制度的存与废,这必须是把“个人之尊严”作为基础而围绕“刑罚的本质”所作的讨论。尽管如此,在今日的日本的死刑存废论像“错判”或者是“舆论”那样地,对于离开了刑罚论的论点,出现反复争论的倾向。可是,被“错判”以至“舆论”所“缠绕住的死刑论”,不管其本来意图如何,却被其“缠绕”而自我束缚住了。因为与错判结合在一起的死刑是不可能被容忍的,所以就等于是死刑的本质反而不明确化地被错判的问题所同化所解消掉。再有,死刑的是非如果被替换成舆论之赞成与不赞成的时候,法就变成数与力的控制,死刑论将仅仅变成现象论以至现状追认论了。这一点,应该可以说成是死刑存废论的“扭曲现象”。关于其“扭曲”的原因,不能避开它而讨论问题。
(二) 刑法修正与舆论
1.支持存留死刑的基本见解的代表性意见,刑法修正的法制审议会刑事法特别部会之立场有如下说明:“不言而喻,死刑的存废问题,不仅在刑法中,就是在整个法律制度之中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迄今为止,已经积累了世界各地从所有的角度对它进行的研讨,而本部会(法制审议会刑事法特别部会)也重新研究了犯下凶恶犯罪的人的道义性责任、对人命尊重之要求、对被害人感情的考虑、死刑所具有的教育性效果以及犯罪抑止力、现在的犯罪形势、国民对死刑的感情、错判之可能性以及在各外国的立法以及运用趋势等各点,虽然也出现了主张全面废除死刑的意见(第二次案第32条,第34条另案),但凶恶的犯罪现在还没有绝迹,据1967年总理府所做的全国舆论调查来看,在国民之大多数(70%)希望存留它的现阶段,认为立即全面地废除它不适当,这种意见很强烈,因而决定存留死刑(注:法制审议会刑事法特别部会,修正刑法草案附同说明书(1972)121页。另外, 该部会的构成成员中死刑存留论者曾占主流,就此问题参照菊田幸一《死刑废除,日本之证言》(1993)10页。)。”
关于这一审议决定,死刑存留论者之一的三原宪三教授,引用了齐藤静敬教授的见解(注:齐藤静敬:《死刑存废之理论与系谱》法律时报第42卷第6号(1960)20页。), 却认识为:“‘在刑事法部会上,委员的多数,愿意在废除方向上考虑死刑。这一点基本上一致了’,可以看成在实质上将是朝向废除死刑前进了一步吧(注:三原宪三:《死刑存废论的法律性根据》创价法学第7卷第1号(1977)138—139页。)”。可是,表明了与其相反评价的是死刑存留论者植松正博士。即:“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是以高度的专家集团所构成的法制审议会刑事特别部会中在”修正刑法草案“的审议上议论死刑存废之际,实际是压倒性多数(回避表示票数)委员表示支持以此通过了存留这一个事实”。“这一点并不仅仅是桌上论或追随流行的公式论,而是依据日夜专心搞犯罪问题处理的职务上之实际感受来表决的,在这一点上,也存在特殊意义(注:植松正,前载注(10)7页。)”
这两项相对立的评论,对构成其前提的事实在内容上未必形成矛盾。可是,关于同一个决议却在存留论和废除论的立场下强调了正相反的两方面。毫无疑问,这里表示出死刑存废论对立之深刻程度。总之,存留死刑的决议,最后确实是考虑到大多数国民意见,但因此原故也就遗留下问题。
2.关于这个问题,《修正刑法准备草案》的理由书说明如下:
“关于死刑存废,因为死刑之废除是世界性倾向,也有认为应该废除的意见,但是准备会的多数人认为在一旦将来国民对法律性确信倾向于废除死刑之际,应该废除死刑,对此没有异论,但在现实的立场上以现状为基础考虑的限度内,不得不把死刑作为应予存续的事物。”(理由书116页)
这样,在以国民的舆论以至法律性确信为其基础的“现状承认论”这一点上,“修正刑法准备草案”也好“修正刑法草案”也好,两者基本上表示相同方针。但是,前者所说的“将来国民的法律性确信倾向于废除死刑之际,对于应废除死刑的问题上没有异论”定成这样的宗旨,未必是明确的,理所当然地会产生疑问。它乍一看来又好像是表示废除死刑的方向似的。可是,笔者认为如果它同时是经常地依附从属于国民的舆论等的话,向国民询问将来刑法的应有方式,就不能说草案立案人完成了核心性的“基本职责”。这项疑问关联到这里所说的“国民的法律性确信”究意是什么?假如它是表示调查舆论时对象人的意见的话,国民之多数倾向于废除死刑这在最近的将来能否会有是个疑问吧?如果是以此为前提的见解,它又可能是“以舆论为保护伞”的彻底的死刑存留论。再有,假定说“国民的法律性确信”意味着学者、法律工作者等专家为中心的国民之意见的基本一致的话,那时候废除死刑由于除去了墙壁,当然是可能的,这不过是表示了不言自明的结论而已。这样的话,不论怎么讲,都不能认为它是明确表示了有意义的将来的方针及其论据的。
3.另外,“修正刑法草案”中的刑事法特别部会的“死刑存留”说明中,在它的开头写有“犯了凶恶犯罪的人的道义性责任”,另一方面又强调了“凶恶的犯罪至今尚未绝迹”。因此,如果是把结合报应刑论以及刑罚积极主义的“道义性责任”使之凶残的犯罪人负担的话,只要是凶残的犯罪不“绝迹”就等于是不得不永远存留死刑了。相反,如果凶残的犯罪一旦没有了,则死刑会失去其适用之余地可能就会到达事实上的废除,但它并不是废除死刑论而不外乎是存留死刑论的立场。因而,就不能不研究构成其前提的“道义性责任论”的妥当本身了。
总之,关于以舆论为支持乃至国民对法律的信心作为死刑存废之论据的意义与是非,进而在续稿构成值得研讨的课题。在这里,仅仅涉及一下其核心点。与“刑法修正”结合的死刑存废论,因为是“法律修正”的问题,因此原故也有可能依据考虑到“舆论”动向的“现实论”。可是,与“修正程序”的问题,姑作别论,而还能够把“论”作为是死刑存废的“实体性根据”吗?唯有这一点才是问题。
(三) 死刑制度的运用
1.在日本国,例如于江户中期德川家重(1745—1760)的时代室鸠巢门下的炉东山(芦野德林)著有《无刑录》(14篇18卷)(注:关于其刑法思想,据小野清一郎《刑法的历史与理论》刑法与哲学(1971)145页,认为:“那虽然不是功利主义性质的目的刑论,教育刑论, 但也可以说曾是超经验性质的目的刑论,深层意义上的教育刑论”。另外,关于无刑录,据1985年文部省科学研究费综合研究(a )《现行刑法典的成立过程》,至岩手县东磐井郡天东町涩民的芦东山纪念馆时购得的东山研究3集—5集(1982—1984)等作了参照。进而,关于无刑录的研究工作,由我们系的橘川俊忠教授现在在做着研究。)。据认为这本书由来于刑律的君主思想(是一种教育刑论),在庆应4年(1913 年)神田孝平介绍了西洋的废除死刑论,明治8年(1922 年)津田真道著有《死刑论》。尽管有开始得这么久的死刑废除论(注:参照迁本前载注(24)6页以下。),而在今天的现行刑法之下仍然存留着死刑制度,支持了存留死刑的是,以此为符合宪法的判例以及后期旧派立于道义性责任论的学说,同时还有现行刑法典及其运用。
2.在已实现了废除死刑的西欧为中心的各国,作为绝对性法定刑曾规定谋杀罪为死刑,为了回避谋杀必须课以死刑这种处罚的僵硬性,可以说法律方面曾经强烈要求应该废除死刑。与此相反,在日本的现行刑法中,作为绝对性法定刑的死刑,唯一在通敌卖国罪上被定下来了,可是也没有谋杀罪的规定,即便是杀人罪,强盗杀人罪的规定也是,只极限于实质上罪责很重的时候才可能选择死刑。这样,在日本的实际法务上,即使是关于适用死刑现实上构成问题的主要犯罪类型“谋杀”(所说凶残的杀人),死刑的选择适用在近年每年只压低在宣判几件上(注:关于近年来死刑判决的动向,参照了加藤松次《最近的死刑判决书宣判之实情》法律论坛第43卷第8号(1990)31页。 松本一郎《永山案件以后的死刑判决动向》,祝贺八木国之先生古稀论文集,刑事法学之现代性展开(下卷,刑事政策编,1992)166页。)。 象这样的刑法的有弹性的规定和谦逊的运用的原故,尽管高谈死刑废除论,但和各外国不同,可以说不曾有过废除死刑是作为迫于现实的不可缺少的政治性课题而动摇了社会的问题(注:再有,据立足于死刑存留论的渥美东洋《日本现行的死刑制度应该废除吗?》刑法杂志第35卷第1号(1995)105页讲,世界上废除了死刑的各国几乎全部都把死刑定为了必要刑这不单是偶然,而可以看做是,正由于是无视个别情况的僵直的死刑量定国民表示了拒绝反应而招致了废除死刑的结果。可是,谋杀罪的规定比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将应加重刑罚的情况类型化了。所以假定渥美教授的理论正确的话,则应修正其加重类型的规定方法以便能够适应个别情况而成为应该维持死刑了。但是废除了死刑的国家是未曾采用类似这样途径的。而且,在并不是必要刑(绝对性法定刑)而是作为选择刑(相对性法定刑)的死刑上,只要是以死刑与自由刑(允许假释的无期刑)之间的决定性差异为前提的话,在这里,不同于通常的量性界限的,足以划出质性界限的量刑标准就必要了。因此,以其标准的不明确性为理由的适当程序违反(宪法第37条)的问题,就可以关于作为相对性法定刑的死刑产生出来。关于这个问题参照岩井,前列注(8)91页、101页。)。就是在今天,日本的死刑废除论,若和关联奥姆教的大量杀人案件的不安和骚动相对比的话,甚至呈现了是不是死刑废除条约的“外来压力”之观。
3.死刑作为“政治犯”的镇压手段等被滥用的情况,在今天已不能太考虑。但是,不能忽视这种现象,就是在社会上不明显存在的差别(社会性抹杀)的手段上利用死刑的可能性总是在“凶残犯”这一名义之下存在。而且,在对于谋杀罪废除了死刑的各个国家,即便是如果是为了取得财产等利己性目的坦然地无视人命的强盗杀人及杀害没有特别责任的数个被害人的这种凶残案件的场合,死刑也是不能执行的了。无视这样的国际比较,在仍然号称治安良好的日本,恐怕可以说轻视死刑废除的问题,就是否定“个人的尊严”的问题。
(四) 报应刑的正义观
看起来好象大体上承认“个人的尊严”但仍然肯定存留死刑的思想深处,潜藏着一方面是形成报应刑论基础的难以抑制的朴素的“复仇感情”以至“报应(补偿)性正义观念”,另一方面是来自对死恐怖的死刑的“犯罪威吓力”以及对“一般预防效果”的确信。这一确信成为支持舆论的“国民性确信”之同时,结合支持死刑存留论的报应刑论,预防刑论的理论化。
例如,平野龙一博士一边排斥新派刑法理论一边拥护旧派刑法理论,使法律哲学性思想和经验性研究相融合,奠定了死刑存留论基础。在此际应予注意的是,如下的自白:
“既然论述死刑,虽然我想亲自看一次执行死刑的场面,可是,对于我来说,怎么也鼓不起这个勇气,我由衷地认为,死刑不应该有。”
“可是,……看见残酷的杀人案件时,我又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忿怒。于是我想,这样杀死人,将可以允许自己受死刑认为是不当的吗?(注:平野龙一:《死刑》(法律学体系法学理论篇12、1951)5页。 )”
在此限度之内,古典性的论调连直至最近也仍然在继续表明。本江威熹检察官,从他接触因杀人案件要求极刑的被害人亲属的谈话的经验,作如下陈述:
“我认为,复仇观念也不能就说是历史性的,仍然是本能性的人类感情”,“我认为被害人亲属要求犯人死刑的感情是正确的。我认为是符合正义的,我甚至认为可能的话,满足他们的想法”(注:本江威熹:《关于死刑的刑事政策性意义》刑法杂志第35卷第1号。)。
在这里,表现出一幅站在被害人一方的检察官形象。可是,为什么如果是“本能性的人类感情”的话,就是“符合正义的呢?笔者认为,正是这样的”报应性正义观念“好像就是共通于死刑存留论的核心。如前所述,内田文昭教授也认为无故杀死人的人不能自行主张生存的权利,(注:内田前载注(9)80 页。)而和平野博士论述了同一宗旨。可是,这一说服性的逻辑,(注:据作为其代表性论者植松前载注(10)16~17页。”所谓废除死刑,这样的人恐怕不外乎是这样的。那就是要作出这样的法律,对这个犯了极坏的犯罪-譬如说企图要残杀一百万人的人,即使对于这样凶手,要作出只保障该犯人生命的这种法律来。这能说是正义的吗?这恐怕是人道论的伤感之类吧。即使对于这些作出同于猛兽行为这类人,正由于他偶尔蒙上了一张人皮,因此就说要比猛兽必须对他尊重其生命,这就不得不苦于找出其根据。猛兽没有理性。从法律上来说,他是相当于无责任能力者的存在。与此相比,当我们面对虽然保存了发达的理性,却又敢于干出象猛兽一样的可怕残暴行为的,我们究意应该把什么作为理由,还有犹豫选择死刑的必要呢?正如在这个逻辑上所表示,所谓死刑存留论是把责任能力之存在为理由,把犯了凶残地杀了人的人象猛兽一样杀掉的这么个主张。在这里完全忽视了这一点。那就是正由于他有责任能力,因而有由于以刑罚导致的规范性动机而复归社会的可能性。)即使不是正当防卫,也不外乎是说“杀人者可以杀之”在法律上也是正当的这种(需要论证)主张。这一逻辑如果没有“同害报复”(塔里欧)之承认,是能够成立得起来的吗?为什么,在法律上按说已经被一般地否认的塔里欧和绝对性报应刑的正义论为什么只是在“死刑的正当化”之际,就能够顺利地复活呢?
2.刑法是以合理地限制无边际的私仇而作为公平刑确立起来的。
即便从我很少的经验来讲,被害人亲属的复仇感情是没有止境的。下面是一桩医疗案例。患了癌症的母亲由于医生不适当的措施(忽略了住院当中的受伤事故)因受伤受到激烈痛苦之后以癌为主要原因逝去。死者亲属在那以后执意寻找已出走去向不明的医生,直到偶然发现继续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医疗错误事故赔偿的民事审判终于以和解终结。据说,有一段时间曾想到和医生互刺死去。腿脚不好的家父横过马路时被高中生驾驶的摩托冲撞而负了重伤到一年后逝世时,我们这些家属的心情,有一段时间也曾经是接近于前述死者家属人们了。这是要求补偿不可恢复的无处发泄的忿怒。这样的报应感情,即使不是来自凶残的杀人案件的被害亲属等,我们也听到不少。可是,我们归根结底不能够认为,把这报应感情纯化于单一的报应刑以此就可以使死刑等的刑罚正当化。至少,同害报复的不合理性是不待阿尔徒尔·考夫曼所示(注:考夫曼,前载注(14)1025—1028页)即自明的,下面讲一讲从田宫裕教授论文中的引用。
“如果把同害报复按字面所写贯彻的话,对于暴力犯则施以笞刑(译注:古代竹鞭刑,始于前汉文帝),对强奸犯则去势,断种,对通奸则做摘除子宫手术按说是可以想到的,然而时至今日又有谁会把这些东西作为刑罚予以肯定呢?”(注:田宫裕:《犯罪与死刑》庄子邦雄等人编,刑罚的理论与现实(1972)169页。)
“车辆轧死人”的时候(行业过失案件)也要进行同害报复的报应主义,对此会有疑问和抗拒吧。可是,更为正确地说,如要把同害报复书面所示而予以实现的话,那就要被杀的人起来把该杀人犯杀死。但是这件事很清楚是绝对不可能的。例如,强奸的被害女性怎么做才可以说是对于加害男性的同害报复呢?关于强奸被害,“第二次强奸(secondrape)”成为问题。可是这并不是在强奸上特有的受害。有一个过往甚密的熟人,他在高中的时候,由于无缘无故在火车站站台里被人殴打打倒在毫无抵抗的状态下被人骑在身上又挨打。因为很多路人都视而不见不来帮助他,由于这种屈辱感,很长时间内陷于丧失自信心和不信任人,直至已经恢复后的今天,据说还常被那件事的恶梦魇住。类似这样一些暴行案件,依据报应刑不会愈合受害人的心灵创伤。
3.恶以恶报的“平衡化”的报应性正义是植根于人类感情的根深蒂固的平衡性感性。它即便能够构成受害人心理的补偿,但却不能成为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等物质以至现实的补偿、修复,只不过是在社会上再生产双重损害而已,因此,同害报复以至绝对性报应刑之类的民刑未分化的正义,作为法律制度曾经有必要社会性地合理(幸福与利益)化。在此意义上,假定说历史上也曾经甚至有过,死刑作为由加害人不能支付赎罪金时的代替手段(注:平野,前载注(33)10页参照。)的话,刑法(公刑罚)作为应该补充民法(由于不法行为的损害赔偿)的内容而发展,此事可以说是民刑之机能分化有了进展。这就是刑法的“补充性原则”。此际,同害报复上的“对侵害依据侵害之平衡”转换为损害赔偿上的“对侵害依据填补之平衡”,据此,作为其补全的刑罚中“预防”的机能是比“补偿”强化了的,假定这种民刑分化的图形在根本想法上是妥当的话,随着由于“个人性自治”的民事审判制度之补全,可以说,从报应刑论向目的论之转换从法律制度整体来说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合理发展。从此意义上说,向报应刑论回归,可说是刑法的返祖现象。
可是,却不能够从目的刑里完完全全地消除报应性机能。第一,因为不能褒奖,鼓励犯罪,即使要立足于教育刑论,也只好对于犯罪预定出作为其危害痛苦的刑罚来。(但是,需要为了缓和其标示效应,不使刑罚单单止于危害的策略。)第二,由于有效地限定了因个人尊严而要求无止境地预防、抑止,所以只有把过去的犯罪作为前提而确定刑罚的需要与否和质量(刑种、量刑)。这个机能可以被罪刑法定和比例均衡的原则所扬弃。可是第三,在损害赔偿不能完全履行的场合,其补偿机能则再度要求以危害报应予以偿还。尤其是因为杀人的生命之剥夺,本来就不能恢复,因而是无法补偿的。杀人的场合特别地强调刑罚的报应机能,可以说在这点上有其合理理由。就是说,平静死者亲属痛苦的手段是极其重要的,而决定性的事情是被杀害的被害人的生命对于本人来说是不能够恢复补偿的。
尽管如此,即便把杀人的报应问题正当化,问题也解决不了。
第一,民事损害赔偿,就是在生命以外的利益侵害的场合,也是不一定都完全履行的。因此,如果是复归到绝对性报应的话,那它就是关于杀人以外的侵害也变成同样了。失去的自由和名誉严格地说也是不能恢复而能赔偿的。第二,生命是绝对不能恢复的,即使求代替其填补的报应,因为因此而失去的生命也是不能恢复的,所以正因为把生命的尊严(不能恢复的价值)作为前提,报应(双重侵害)才包含矛盾。为了从此矛盾中解放出来,只有把犯罪(杀人)者的生命解释为不值得予以法律保护的生命了。并且,死刑又不是象正当防卫那样的在保全法益上不可缺少的行为,而是有计划杀人的一种。把它从一般预防和特别预防的观点来看可能正当化吗?这一点,在续稿上会成为应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