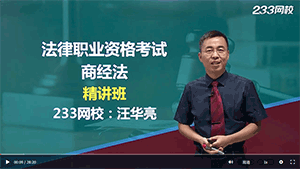一、关于防卫权问题-来源及其范围
防卫权是由人类的防卫本能逐步发展而来的一项法律上的权力。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分散型的个人防卫本能向具有社会整体认同意识的法律权力进行转化的过程,实现了作为一种原始复仇状态的无节制行为朝着合乎人类理性和社会需要的有限制法律行为的转变。由此,防卫行为就不再是不受任何拘束的纯私人行为了,需要受到社会道德和法律规范的多重制约。刑法在对防卫行为的合法性作出确认的同时,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对人们行使防卫权的范围、条件、合理限度等进行规定,以规范人们的行为,防止因其权力滥用而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破坏法治的秩序。
在现代国家里,当合法权益遭受到犯罪行为侵害时,受害者通常需要借助国家的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的诉讼程序,通过刑罚权的行使才得以维护,消弥已经受到的损害。这是一种被称为“公力救济”的强制性手段。禁止公民擅用强力,强制手段由国家行使,这已成为法治社会的普遍要求。然而,“公力救济”并非永远最为有效的,它同样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性和结果上的不完整性,为了弥补“公力救济”的不足,达到全面维护合法权益的目标,各国又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特殊条件下的“私力救济”行为的合法地位,允许公民在来不及请求司法机关予以保护,而合法权益又面临紧迫侵害时,可以有节制地予以防卫反击,以阻止损害结果的实际发生或者将可能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的程度。因此,以“公力救济”为基础,以严格控制下的“私力救济”为补充,已经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一种普遍观念,并进一步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化设计,这就是刑法上或者民法上的正当防卫制度。
不过,就刑法角度来看,各国对防卫权范围的规定其实并不一致,刑法学者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至少涉及到两个基本问题。
其一,在刑法上,是否应当规定公民为了维护公益(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而行使防卫权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维护国家及公共利益的责任本应属于国家特设的公共机构,一般公民没有此项冒险的义务,国家不应通过立法将其纳入公民防卫权的范围,否则,会有推卸国家公共机构责任之嫌。基于正当防卫系“私力救济”手段的认识,很多国家未在刑法典上对此予以规定,通常只是笼统地允许公民为了维护“自己”或者“他人”的权利而行使防卫权。我国刑法历来允许甚至在本质上倡导公民为维护公益而对不法侵害行为进行正当防卫,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典,更将“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权利免受侵害作为公民行使防卫权的前提。在我们看来,为维护国家、社会及他人利益而进行的防卫,是一种典型的“见义勇为”行为,立法将其纳入防卫权,并非要强制公民必须照此行事(因为刑法上的防卫权力从来不是一种法定义务),而是出于扩大公民个人权力在法律上认可范围的需要,它与正当防卫作为一种法律许可并予以保护的“私力”的本质并不矛盾。而在实际生活中,公民也不会因为“见义不为”而遭致诸如法律上“不作为”的责任。笔者注意到,即使是那些在刑法典上仅仅规定为防卫自己或者他人权利才可行使防卫权的国家,他们在学理及实务中,也存在着将“他人”一语作扩大解释,以适应实际防卫需要的情况(注:譬如,有日本学者认为,所谓“他人”,并不限于自然人,应该认为是包括法人和其他团体在内,所以也允许私人为保护国家法益而进行正当防卫。为保护他人法益而进行正当防卫,叫做紧急救助;为国家而进行的正当防卫,叫做国家紧急救助,也有叫做国家正当防卫的。本文作者认为,“国家紧急救助”或“国家正当防卫”的提法有所不妥,易致人们望文生义、产生异义。参见(日)福田平、大仁合编《日本刑法总则讲义》(中译本)第91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
其二,在公务活动领域,是否应当确认公务人员也有职务防卫权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在我国新近的刑法著作中少有论及。 不过, 发布于1983年《关于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中实行正当防卫的具体规定》(注:该《规定》于1981年8月1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五个部门联合签署、发布。在当时,这类形式的文件属于司法解释。),则表明了我国在司法实务中予以肯定的立场。故此,一些学者当时称它为“正当防卫的特殊形式”(注:参见陈兴良:《正当防卫论》第18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版。),还有人撰文专门论述了一般正当防卫与这种特殊形式正当防卫的异同之处(注:如刘普生在《司法人员与非司法人员正当防卫之异同》一文中,将它们的异同概括为目的相同而责任不同、意义相同而性质不同、方法相同而手段不同、构成条件相同而对象范围不同、过当条件及刑事责任相同五个方面。载《法制日报》1988年9月18日第3版。)。基于同样的认识,1996年10月10日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专门设立了一个条文,对公安人员、武装警察在执行公务期间行使防卫权的问题作出了明文规定。但次年3月14 日正式通过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却又删去了这一条文。笔者认为,取消“职务防卫权”的规定,将防卫权仅仅赋予公民个人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公安人员、武装警察在执行公务期间遭遇暴力侵袭或为制止针对国家、社会、公众利益的侵害而进行的反击(必要时甚至使用警械和枪支),完全是一种履行职务的行为,是其职责所在。倘若其反击行为没有依法进行,譬如滥用警械和枪支(诸如违反《人民警察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规定》的行为),或者未尽职守,没有履行应尽的反击义务,均将遭致法律上的不利后果甚至可能承担刑事责任。而所有这些,都与法律赋予公民个人进行“私力救济”的防卫权的本质大相径庭。事实上,履行职务的反击行为具有明显的“公力”性质,其实施过程应当受到格外严格的监控,如果我们在法律上规定了“职务防卫权”,并且将其与“公民防卫权”相提并论,那无异于再度鼓励和促进国家权力的积极行使,导致强者更强,公民合法权利的有效维护将变得愈加艰巨和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严格限定防卫权的范围,是防止国家权力滥用、切实保障人权的需要。
二、关于防卫要件问题-正当性及其制约
设立科学合理的防卫要件,是防卫行为获得社会认同并取得正当性的前提。正当防卫的要件,建立在刑法典明文规定的基础之上,它是正当防卫法定概念的展开及其基本界限的实体把握。我国现行刑法典第20条第一、二款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据此,笔者认为,目的的正当性、侵害的紧迫性、客体的特定性和力度的有限性,是我国正当防卫的几个基本要件。
(一)防卫目的的正当性
刑法上设立正当防卫制度的出发点,在于强化“私力救济”;及时维护合法权益。与这一立法意图相适应,刑法上要求构成正当防卫的主观要件必须是防卫人具有维护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的特定目的。如果目的不正当、不合法,只是在行为的形式与外观上符合防卫的要求,同样不能得到刑法上正当防卫的评价。在司法实务中,由于目的不正当而不能成立正当防卫的情形主要有三种:其一,是挑拨防卫,表现为行为人基于加害的意图,故意挑逗、引诱对方实施不法侵害,尔后假借防卫之名损害对方利益的行为。挑拨防卫具有正当防卫的假象,因此,证据调查及其判别就成为司法实务中的一个关键。其二,是巧合防卫,即行为人在不明知侵害行为正在发生的情况下,针对侵害人所实施的故意加害行为。例如某甲正在强奸某女,乙却并不知情,误为自愿行为。乙出于对甲的素仇,遂棒击其头部,致其停止强奸、重伤倒地,乙亦随即逃逸。巧合防卫虽在客观上吻合防卫要件,但因行为人基于不法侵害的意图,故不能以正当防卫论定。其三,是相互打斗,即双方基于互伤对方的目的而进行的相互之间连续不断的殴击及厮打行为。将相互打斗排除在正当防卫之外,是将其行为意图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人为地予以分割)来进行考察的结果。不过,我国刑法学界并不绝对否定以相互打斗为起因的防卫行为存在的可能。一般认为,如果一方确已放弃侵害(诸如求饶、逃离等),而另外一方依然不断加害,致命其合法利益受到严重危害时,放弃侵害的一方仍然存在着防卫反击的权力,对其依法进行的防卫,应当确认并予以法律上的保护。
(二)不法侵害的紧迫性
有侵害才有防卫,有不法侵害的紧迫性,才会有防卫反击的必要性。因此,不法侵害,事实上已经成为实施正当防卫的客观前提。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上,我国立法上却使用了“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这样一个显得有些抽象和原则的用语,从而给司法上的认定带来了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