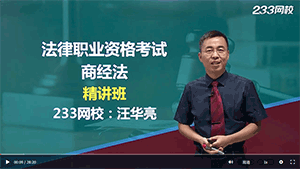罪刑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已成公里,其现代意义上的司法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即“凡是自由民除经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财产、剥夺其法定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和逮捕。”这里就蕴涵这罪刑法定的思想。到了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针对封建刑法中罪刑擅断、践踏人权的黑暗现实,更加明确的提出了罪刑法定的主。之后被誉为“刑法之父”的贝卡利亚在其著名的《论犯罪与刑罚》中指出的“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是刑罚”,这一观点则至今仍为刑法学者频频引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罪刑法定这一思想由学说转变为法律,在资产阶级宪法与刑法中得以确认,成为世界各国刑法中最普遍的一项原则。
对于中国来说,罪刑法定是姗姗来迟的。1979年刑法中仍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相反却在其第七十九条规定了有罪类推制度;直至1997年全国人大对79年刑法作了大规模的修订,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即修订《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由此,学术界和司法界处处洋溢这赞誉之声,罪刑法定的确立并加以适用对我国的法制建设来说无疑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
然而负重之骥难以猝然站立,在中国这头雄狮的血管立流淌的从来就不是法治的血液。在人治的天空下,中国的政权机构积淀下了太多命令高于法律的习惯,积重难返;中国的国民被千百年来的压制所束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罪行法定的贯彻实施便难上加难了。
而今,法治的车轮已经滚过了21世纪的最初几年,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政府强有力的鞭策下成效斐然,但存在的问题也令人触目惊心。
要论述罪刑法定,就无法避开刑法的结构问题。这是罪刑法定能否在一个国家得以有效实施,能否真正惠及国民的关键所在。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罪与刑的结构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种:
一、罪状设计严密,刑罚严厉(又严又厉);
二、法网不严密,刑罚不严厉(不严不厉);
三、法网严密而刑罚不严厉(严而不厉);
四、刑罚严厉而法网不严密(厉而不严);
结构决定了功能,不同的刑法结构具有不同的刑法功能。法网严密,有助于刑法保护社会功能的实现;刑罚宽缓,则有利于刑法保障人权功能的达成。因此,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是当今世界刑法发展的走向,至今已为多数西方国家所采用。我国的刑法结构应该说是厉而不严的。在我国现行刑法中,重刑(包括死刑和自由刑)所占的比例相当大,在刑法分则中,几乎每个犯罪形态(罪种)都能使罪犯的生命权遭受剥夺。死刑的泛滥使刑罚失却了预防犯罪和教育罪犯的根本意图,既失于人道,又不利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西方200多年的刑法发展史表明,刑罚趋缓是刑法演进的规律,减弱刑罚的调控强度,实现刑罚的轻缓化已然得到学界的共识。因此,在中国未来的刑事立法中,应该适当加大罚金在刑罚体系中比例,合理限制有期徒刑的适用范围,特别是要削减死刑。
法网不严是我国刑法中罪刑法定举步唯艰的核心问题。现在,中国已经加入WTO,但是我国现行的犯罪形态却未得以有效的调整和革新。如而今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的犯罪问题在我国日益严重,而在我国的制定法中,却仍未增设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的罪种,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要严格遵循的罪刑法定,对这种犯罪类型,定罪便无从谈起;而要对之予以定罪,有罪类推的幽魂便惟有死灰复燃了。这无疑将使我国的司法实践陷入尴尬之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类新型犯罪层出不穷,对之增加与之相应的罪种,便成了重中之重。
法网疏漏,最大的疏漏在于缺乏违宪审查机构。违宪是最严重、最具社会危害性的犯罪,宪法独特的法律地位使它与其他部门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违宪案件一旦出现,将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使部门法上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反思
相关阅读
-
司法考试笔记辅导:刑法章节笔记汇总
-
刑法辅导:什么是罪刑法定原则?
-
2007司法考试:每日一练(刑法)
-
专家刑法辅导:刑法目的把握最关键
-
法律司法考试答疑精华之刑法专题
-
07年司考专题之刑法全真模拟试题及解析(二)
-
07年司考专题知识之刑法全真模拟试题及解析
-
万国:2007年司法考试刑法试题分析
-
2007年司法考试刑法命题特点与规律探索
-
2007年司法考试刑法冲刺点题班讲义
-
新东方:刑法犯罪主体部分黄金考点
-
司法考试刑法犯罪主体部分黄金考点及口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