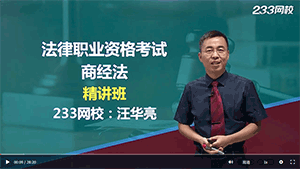这样,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有法定行政解释权的主体主要有如下几类:1、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包括法制机构);2、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3、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
但是,我国在各具体法律法规中关于行政解释主体的设定实际上远远超出了1981年《决议》以及国务院“两个条例”规定的范围。从各法律法规明文“授权”的行政解释主体看,主要有以下几种:1、国务院②。2、国务院主管部门。如1982年4月13日国务院颁布的《公正暂行条例》第29条规定:“本条例由司法部负责解释”。3、国务院直属机构。如1988年1月3日的《商标法实施细则》第48条规定:“本实施细则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4、国务院某个办公室。如1993年7月19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实施办法》第30条规定:“本办法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进行解释”。5、省级人民政府,如1985年2月8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暂行条例》第9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广东省人民政府根据此条在1985年3月29日的《广东省城市维护建设税实施细则》中对《暂行条例》作出了大量的解释性规定。6、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如上述《广东省城市维护建设税实施细则》第15条规定:“本细则授权广东省税务局解释”。7、省会市人民政府。如1995年9月29日福州市人大常委会颁布的《福州城市部分事业设施建设和保护规定》第14条规定:“本规定由福州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8、省会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如190年杭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杭州实施土地管理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7条规定:“本规定由杭州市土地管理局负责解释。”
在上述行政主体中,除了1、2、5、6、7外,其他解释主体所作的行政解释均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这样便产生了一个问题:行政解释的主体是法律授权的行政机关,但是是否任何法律法规均可作出此种“授权”?答案是否定的。行政解释是行政机关对立法机关及较高层级的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解释,究其实质无外乎是执法者、释法者如何对待立法者的问题,它涉及到行政和立法的关系问题。对这个关系问题,既不能由制定一般法律的立法者决定,也不能只听信释法者的一面之辞,而应由国家的宪法及宪法性文件来定夺。因此,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的形式决定有关法律解释问题是不妥当的,由一般法律法规确定各自的解释主体更是于理不符。
2、有关行政解释对象的规定不明确
依据1981年《决议》、《行政法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有关规定,行政解释的对象似乎主要包括与审判和检察机关工作无关的其他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包括部委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但是,对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的文件(规范性文件)是否应列为行政解释的对象,法律法规规定不甚明确。1993年3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行政法规解释权限的程序问题的通知》第3条规定:“凡属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的解释问题,仍按现行做法,由国务院办公厅承办。涉及行政法规的问题国务院办公厅可征求法制局的意见;涉及法律解释的,按照《决议》办理”。根据这个文件,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的文件似乎应该作为行政解释的对象。但是国务院办公厅的这个通知效力如何,国务院办公厅是否有权对此作出规定呢?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3、有关行政解释表现形式的规定付之阙如。
1981年《决议》及相关法律法规都没有有关行政解释应该以何种形式作出的规定。实际生活中,有关行政解释的表现形式相当繁杂,如“通知”、“补充通知”、“暂行规定”、“复函”、“复文”、“答复”等,反映了行政解释的混乱,同时也造成了行政解释形式的不统一。
(二)行政解释与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关系不明确
1、行政解释与立法解释
根据1981年《决议》的规定,凡关于法律、地方性法规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相应的立法机关予以解释;凡关于法律、地方性法规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相应的行政机关进行解释。即立法解释是与行政解释的范围分别为“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和“具体应用”。表面看来,二者各有分工,不可能出现重叠交叉现象,但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实际情况远非如此:(1)法律是应用中的解释,存在于法律制定通过后的法律实施领域。法律未经应用,就不会有真实的而非想象的解释问题出现。[9](2)具体应用中的解释主要就是“明确界限”。要弄清应该如何“具体应用”法律,往往要对法律条文本身“进一步明确界限”,甚至可以说,“具体应用”法律过程中所作的解释,主要就是对法律条文本身的“进一步明确”。因为只有法律条文文字含义的模糊、不明确,才需要通过法律解释进行确定,界定其界限。对界限明确的条文,在应用中是不需要进行解释。如全国人大常委会199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4条所称的“关联企业”和“独立企业”,正是由于其界限不明,才需要国务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中对“关联企业”和“独立企业”予以界定,明确其界限。因此,在有些情况下,行政解释的立法解释的范围区分就显得不是那么明确。
正是由于行政解释与立法解释的范围区分不是那么泾渭分明,二者在实践中极容易出现交叉和冲突现象:(1)行政解释对立法解释的侵害,即行政机关对只能由立法机关作为出解释的事项进行了解释,尤其表现在国务院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权的侵害。“虽然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权作了明确规定,但立法解释制度以确立至今,基本上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极少颁布立法解释性文件。”[10]相反,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等行政机关其享有的行政解释权却有呈无限扩大的趋势。(2)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解释权出现竞合,即两者对同一个问题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虽然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立法机关是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关,作为权力机关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撤销与立法不一致的法规、决定和命令,但如何启动立法机关的撤销程序,立法机关怎样行使撤销权,由哪个部门行使撤销权等程序性规定都付之阙如。
2、行政解释与司法解释
所谓司法解释,是指有关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在实施法律过程中,对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所作的解释。
根据1981年《决议》,司法解释的主体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它们只对全国性法律作出解释,对地方性法规的解释不在司法解释的范围之列。因此,行政解释与司法解释的关系实际上是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对全国性法律的解释上形成的关系。
行政解释与司法解释两者关系不明确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行政解释是与司法解释的范围区分不甚明确。1981年《决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司法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对不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问题进行解释。但我国并没有哪一部法律具体规定哪些法律只能由法院、检察院实施,哪些法律只能由行政机关执行。(2)法律对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两者的效力规定不甚明确。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必须尊重司法解释的效力?人民法院在司法审判中应否尊重行政解释的效力?如果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对同一问题的规定出现不一致,该怎么处理?而这些问题直接导致在行政诉讼实践中,一些法院无视行政解释的法律效力,对是否采纳行政解释进行非常随意的自由裁量;在行政执法实践中,有些行政机关完全无视相关司法解释的存在。例如,据报载,在青岛中级法院审理的青岛市技术监督局处罚造假者青岛市黄岛区橡胶总厂二分厂的行政诉讼案中,技术监督局依照国家技术监督局《关于对〈技术监督行政案件“违法所得以非法所得”计算的意见〉具体实施的复函》的解释,按全部经营额认定并没收了非法所得,但法院则认为将“全部销售额”认定为非法所得于法无据,而按照获利额计算非法所得并改变了技术监督局的处罚决定。在本案中,国家技术监督局对非法所得的解释是国务院主管部门对行政执法具体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法院却不承认其法律效力。[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