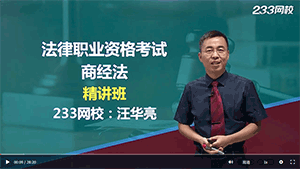一生中“最恨女人”规矩青年因情变成杀人恶魔
第二天,还在生闷气的周元奎听媒人说,女方将在近期到他家“看人户”(当地习俗,结婚前的仪式)。周元奎又看到了希望。4月18日这天,母亲携俞华来到周元奎家,高大的楼房,新潮的家具让俞华的母亲啧啧赞叹。可俞华却在一边和小孩们玩成一片。周元奎于是凑上去一起玩游戏,这次俞华没有躲避,仍一脸灿烂地玩着。尽管没有说上几句知心话,但周元奎从俞华“阴转晴”的表现上感到了满足。俞华母女俩临走时,周元奎按当地风俗,送给了俞华1800元彩礼。可此后,不管父母怎样劝说,俞华对婚事却一直未应允。
俞华软硬不吃的态度,让周元奎担心日久生变。他立即催促媒人传话,若不结婚,便退还彩礼和借的钱。俞华家里穷得叮当响,哪还得起几千元彩礼。为说服女儿出嫁,母亲一遍遍数落家里的困境。在母亲的“开导”下,尚未成年的俞华只得违心地答应了父母的请求。
2002年10月1日,在父母及亲友哄劝下,刚满17岁的俞华稀里糊涂踏进了周元奎的新房。
规矩青年变成恶魔
强扭的瓜不甜。新婚之夜,周元奎和俞华相视无语坐到了午夜,俞华非常厌恶地拒绝了“丈夫”的“非分要求”。
第四天,新郎、新娘回娘家。但是俩脸上却看不到半点喜气。小两口的事也传到了俞华父母耳中。当女儿要离去时,母亲告诫她:“婚都结了,要跟他好好过日子。”
可接下来的日子,周元奎更尴尬了。每天睡觉,俞华总是和衣而睡,不让周元奎近身,连吃饭也不愿同坐一桌,总要等周元奎吃完饭上工后,再单独吃饭。
为讨俞华欢心,周元奎每过几天便给俞华几十元零用钱。可俞华却仍我行我素,对周元奎没有好感。
2002年10月20日,依旧闷闷不乐的小两口再次回娘家。俞华的父母却不再过问女儿的家事。临走时,周元奎突然开口说:“你们这儿离镇上学校较远,让弟弟(13岁,俞华的弟弟俞刚)搬到我们家住,上学要方便些。”面对周元奎的主动邀请,俞华的父母毫不迟疑地答应下来。周元奎原以为妻弟的到来,会让俞华改变对自己的看法。哪知,俞华同弟弟倒是手足情深,但对他仍形同路人。
周元奎家里的“新闻”像长了翅膀很快传到矿上。工友们常常取笑他。原本性格内向、心胸狭窄的周元奎无心辩解,只是更加苦闷了。工友的取笑,妻子的冷淡,连同过去牛珊对他的欺骗,总在周元奎的脑子里转来转去,愚昧的他竟萌生了报复念头:“你不让我好,我也不让你安宁!”
11月2日,周元奎从街上买回三包老鼠药,准备对妻子投毒。可俞华寸步不离厨房,也不乱吃乱喝,周元奎只好放弃了。
11月12日晚,周元奎噙着眼泪,对俞华说了一大堆好话,从从小受苦,到打工挣钱;从建房结婚,到爱妻顾家;从金钱花光,到夫妻有名无分……但他的眼泪最终未能感化俞华,俞华仍然和衣而眠,不久便呼呼进入梦乡。
万念俱灰的周元奎一直呆坐到凌晨3时,见俞华仍然睡得香甜,他发誓:“一定要干掉这个女人!”于是,他拿出从矿上带回的电雷管,安放在俞华的颈右侧,随着一声闷响,俞华身边一片血泊……
周元奎心中充满了杀人后的恐惧。慌乱中他突然意识到,内弟俞刚还睡在里屋房间,若他醒来,自己的罪行岂不很快被暴露?于是,他又轻手轻脚地来到俞刚的房间,下了毒手。
杀死两人的周元奎在慌乱逃窜中,竟一头跌入附近的河沟而不省人事。当他醒来时,才发现自己已被警方抓获。随着诉讼程序的进行,周元奎的人生终于因自己的鲁莽、残忍而走到了尽头……
这场悲剧的原因是什么?是周元奎扭曲的人格,还是愚昧的婚姻观念?法制的力量能够严惩杀人者,但要剔除残存在人们骨子里的思想痼疾,却是最紧迫而又艰难的。
知识和愚昧
人的性格是环境的产物,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些抽象的道理落实到一个具体的案子上,却是那么触目惊心。没有人是突然之间变成一个恶魔的。本案中这个原本老实厚道的农村青年也是如此。女性,在他的头脑里原本是和母亲、温情这些词联系在一起。如果在大哥家,没有遭遇大嫂的冷遇和嘲讽;如果在那个小县城里,没有遭受牛珊的欺骗,他还会不会走向“深渊”,沦落为一个偏执的杀人者呢?可生活是无法预定假设的,它只按照自己的逻辑走下去,无法更改。
可有一些东西,原本是能够改变的。愚昧本不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可以贫穷,但他的精神世界却不一定贫乏。多年以前,当看到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里的主人公,在油灯下苦读小说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这种东西。这样说,并不是希望农村青年都去做文学青年。而是觉得,在知识的阳光多洒落一些的地方,愚昧的黑暗就会少一些。本案中害人者和被害者,都只有小学文化,不也说明了这一点吗?贫穷产生了愚昧,愚昧又孵化了罪恶。这恐怕也是一个通行的公式。让知识之光多一点照耀到偏僻的乡村,而不是只落实在扫盲统计表上,才会生发更多的文明与富裕。知识虽然不能让你立刻发财,但它毕竟可以预防罪恶的孳生。这也许不算是题外话吧?
责编:qinqin
相关阅读
-
妻子请求离婚丈夫反诉长期遭受其性侵害
-
妻子出家丈夫再娶尼姑一怒之下告丈夫重婚
-
北京一中院宣判一起探视权纠纷案件
-
女儿遭强暴夫妻为保女儿假离婚却弄假成真
-
老人黄昏恋子女兴师问罪闹剧开始悲剧告终
-
倔犟矿工打赌嫖娼后以服毒自杀“谢罪”
-
夫妻俩因怕遗产与别人同分杀死养父
-
马岭河事故幸存遗孤监护权纠纷纪实
-
婚姻:利用非典隔离风流少妇毒杀亲夫
-
婚姻:世间无奇不有离婚也雇“枪手”
-
婚姻:大龄男求妻心切相继栽倒媒人嘴
-
丈夫同床要求被拒一盆沸水泼向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