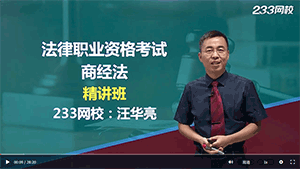被告李某(女,60岁)与遗赠人周某于1965年结婚,婚后夫妻感情较好,未生育小孩,收养一子(31岁,已成家另立门户)。1998年周某认识了比他小30岁的邱某(原告)不久后,二人便租房公开同居生活,直至2003年5月,周某因患肝癌晚期住院治疗。在周某住院期间,一直由李某及其亲友照料,直至死亡。临死之前,周某立下书面遗嘱并经公证将其所得的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金首饰、手机一部和变卖位于某市的房产的售房款的一半等共计10万元遗赠给邱某所有;骨灰盒由邱某保管。周某去逝后,邱某以李某控制前述财产,拒不交付,侵害其财产权于近日起诉到法院,关于本案的焦点:即遗赠人周某遗赠自己的财产(姑且不论周某遗赠自己无权遗赠的效力问题)是否一定有效?争议较大,产生了如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遗赠人周某在与李某尚存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公然与原告同居;且立下遗嘱准备将财产遗赠给与其长期非法同居的本案原告。这一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的民法基本原则和《婚姻法》确立的一夫一妻制原则。在周某患肝癌至死亡时,均由李某及其亲友照顾,而周某却在此期间将全部个人财产遗赠给同居之第三者,完全无视作为自己三十年合法妻子李某的存在,不符合一般的家庭道德,与普通民众的道德理念背道而驰。《民法》作为一国人民思想、文化、观念、传统的集中体现,不能忽视来自民众的声音,否则法律就不能渗入社会实践,不能对人民群众的意识行动产生导向作用。本案中如果机械地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引用《继承法》第16条第一款进行处理,实质上是对遗赠人周某“包二奶”,将财产赠与“二奶”这种严重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给予支持,破坏了我国倡导的社会主义行为规范,使广大群众对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产生怀疑。《婚姻法》修正案颁布后,还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种道德性社会规范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保护第三人者邱某在本案中可能获得的利益,肯定有违《继承法》的立法精神,动摇我国法律的根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继承法》的立法者们在立法时不能预见的。这也是成文法的局限所在。《民法通则》对民事行为的原则性规定,也是在保证引用特别法的规定有违立法精神的情况下,能最终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所以,对本案,根据《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应宣告遗赠行为无效。
第二种观点:遗赠人周某生前所立遗嘱意思表示真实,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且经公证,合法有效,根据《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该条第三款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尽管邱某是第三者,也不影响遗赠的效力,即使是正在服刑的罪犯,也有权获得遗赠。《继承法》并未明确规定“禁止将财产遗赠给第三者(非法同居关系)等不正当关系的无效”。所以,周某的遗赠行为符合《民法通则》第55条的规定,不违反第58条之规定,应是合法有效的。《继承法》是特别法,《民法通则》是普通法,无论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理,还是按民事法律对某一案件所涉及问题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作出规定时,才可适用民法原则的惯例。本案均应适用《继承法》,而不适用《民法通则》。故,根据《继承法》第16条的规定,应确认遗赠合法有效。
第三种观点:根据物权法的原理及《民法通则》、《继承法》的立法本意和立法指导思想,法律应是弘扬财产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以及遗嘱自由的精神,凡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均有绝对地、自由地、不受限制地处分自己的合法财产的权利,这也是国际潮流。对此,我国《宪法》第13条及《民法通则》中有关财产所有权制度均有明确规定。上述法律所体现的指导思想,即自由处分属于自己的合法财产是公民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一指导思想在《继承法》中表现为遗嘱自由之精神。这也是《继承法》规定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的根本原因所在。至于有人认为:周某将自己遗产遗赠给第三者邱某,违反社会公德,遗赠行为无效。显属牵强附会。根据“法未明确禁止的行为即为合法”这一民法施行原则,法律既未禁止违法者或不道德者立遗嘱处分自己的合法财产,也未禁止公民将遗产遗嘱给违法者或不道德者,假如周某将前述财产遗赠给一个正在服刑的赌友,又将如何?其人一定会说,赌博和本案无关,遗赠是有效的。然而“包二奶”、“当二奶”和“做赌友”、“交赌友”均是不道德的,为什么要区别对待?毕竟邱某“当二奶”的行为和她接受遗赠是两种法律关系,两种毫不相关联的法律关系。邱某“当二奶”违反社会公德,但她接受遗赠的权利不能因此被剥夺,除非能够证明:周某是以死后将其遗赠遗赠给邱某作为邱某为其充当“二奶”的交换条件;或者能够证明邱某是以周某死后将遗产遗赠给自己作为充当“二奶”的条件,才可以以所附条件违反社会公德为由,确认遗赠无效。而本案不属此情况。综上所述,应确认遗赠合法有效。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
内容真实的遗赠是否一定有效
责编:onmars
相关阅读
-
计生罚款能否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分割
-
综合案例:案件再审,财产保全能否中止
-
综合案例:夫为妻代理家事行为有效
-
综合案例:此案被告不享有优先购买权
-
综合案例分析:亿利达缘何不担责
-
综合案例:此案能否变更股东为被执行人
-
综合案例分析:乙1公司应否成为被告
-
综合案例:虚假按揭能否构成合同欺诈?
-
综合案例:本案侵权行为客体如何认定
-
综合案例:重大过失责任能否预先免除
-
在有偿合同中违反无偿服务约定是否承担违约责任
-
综合案例分析:王甲应定故意伤害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