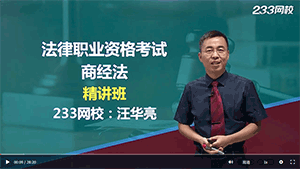受遗赠人唐X等诉汪X等应依双方签订的遗产分配协议取得遗产案
汪X不服判决上诉称:被继承人的口头遗嘱不是其真实的意愿,不符合继承法规定的条件,因此不具有法律效力,故请求二审法院按法定继承处理本案的遗产。
刘北平、唐X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各方当事人所得遗产的份额符合被继承人的遗嘱,故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汪X的上诉。
农七师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继承人汪随义住院治病期间,一直神志清醒,对于后事的处理已向无利害关系的多人表达,其口头遗嘱内容真实,应确认有效。上诉人汪X上诉称该口头遗嘱不是被继承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但未提供证据证实,故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汪X与唐X订立的“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征得了刘北平的认可,应当作为本案当事人对遗产分割的依据,当事人应当按该补充协议的约定分得遗产。
唐X、刘北平虽不属法定继承人,但他们在被继承人生前,尤其在被继承人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尽了照料、赡养义务,依法应适当分得部分遗产。原审判决给他们分得遗产和分得遗产的数额是正确的,但表述他们“继承遗产”不当,应予纠正。
农七师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2000年8月31日判决如下: 一、维持新疆奎屯垦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之第一、三、四、五项。
二、变更新疆奎屯垦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遗产中钱款为33080.12元,由刘北平分得13232元,唐X分得11578元,汪A继承8270.13元,汪随义的遗留家具及生活用品由汪A继承。
【评析】 本案处理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按遗嘱处理遗产还是按法定继承处理遗产。用遗嘱的方式处分遗产,是被继承人生前的意愿,应该受到法律保护。按照我国继承法有关条款规定的精神,遗嘱继承的效力优于法定继承的效力。本案中被继承人汪随义生前立有口头遗嘱,如果其遗嘱有效,就应按遗嘱处理遗产;如果其遗嘱无效,则应按法定继承处理遗产。口头遗嘱是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口授制成的。所谓危急情况,就是不可能进行公证遗嘱、自书遗嘱或代书遗嘱的紧急情况。汪随义是在亡故的前三天立下口头遗嘱的,此时他已病危,不可能立下其他形式的遗嘱,只有在病床上当着众人的面口述了他对自己的后事和遗产如何处理的意愿。这众人当中,有学校的领导,也有同事,他们与本案无利害关系,可以成为遗嘱的见证人。这就是说,被继承人汪随义的口头遗嘱,从形式要件上看,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么,该口头遗嘱是否也符合实质要件呢?根据继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有关条款的规定,口头遗嘱的要件必须符合:遗嘱人在设立遗嘱时必须具有遗嘱能力;遗嘱必须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遗嘱不得取消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继承权,要为他们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遗嘱只能处分被继承人个人的财产。从本案情况看,双方当事人对被继承人的口头遗嘱符合后两个实质要件没有争议,有争议的只是在前两个要件方面,即被继承人汪随义立口头遗嘱时是否具有遗嘱能力,该遗嘱是否为遗嘱人的真实意愿表示。本案事实表明,被继承人汪随义在口述遗嘱时,虽然病情处于危急状态,但他神志清醒,具有遗嘱能力,能够清楚地表达他的遗愿,这不仅为当时在场的胡居民、黄祖民、赵风松等众人所见证,也为遗嘱人所口述的有条有理的内容所证明。被继承人在口述遗嘱时,没有受到胁迫,也没有受到欺骗,完全出于自愿,是其处分自己遗产的真实意思表示。这就是说,被继承人所立的口头遗嘱,在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方面均没有无效的情形,因此应确认有效。既然本案被继承人所立的口头遗嘱有效,就应依法按照该遗嘱处理遗嘱人的遗产,以尊重和体现遗嘱人对个人财产处分的意愿。
本案处理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本案原告、被告和第三人应以何种主体资格分得遗产。从一、二审判决所表述的判案理由和判决结果来看,一审法院将原告、被告和第三人均确定为遗嘱继承人,他们以该种主体资格分得遗产份额。二审法院将被告、第三人确定为遗嘱继承人,而将二原告确定为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他们均以该种主体资格分得遗产份额。根据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这就是说,遗嘱继承只能发生在法定继承人中,只有法定继承人才能成为遗嘱继承人;而遗赠发生在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中,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可以成为受遗赠人。从本案一、二审法院所确认的事实看,被告汪X是被继承人汪随义的胞兄,属于第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被继承人以遗嘱指定将遗产分给汪X一份,依据继承法的规定,其在本案中应为遗嘱继承人,并以此资格分得一份遗产。第三人汪成喜是被继承人的胞兄汪X之子,不属法定继承人;原告刘北平、唐X均是被继承人生前的学生,尽管他们与被继承人有着深厚的师生之情,甚至刘北平与被继承人以舅甥相称,但他们均不能成为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他们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被继承人汪随义以遗嘱指定由他们各分得其遗产一份,依据继承法的规定,他们在本案中应为受遗赠人。这就是说,被告汪X应以遗嘱继承人的资格分得一份遗产;第三人汪成喜和原告唐X、刘北平应以受遗赠人的资格各分得一份遗产。因此,一审法院将原告、被告和第三人均确定为遗嘱继承人,二审法院变更确定二原告为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并以对各当事人资格的确定判决他们享有分得遗产的权利,不完全符合继承法有关条款的规定。
本案处理遇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认定“补充协议”的性质和效力。该“补充协议”产生于被继承人死亡之后、遗产实际处理之前,其主要内容是关于确定遗产大概数额和各当事人分得遗产的比例,可以认为该“补充协议”是各方当事人就遗产如何分配问题达成的协议。案件事实表明,该“补充协议”的内容与被继承人的口头遗嘱的内容基本一致,没有违背被继承人的愿望;而且该“补充协议”是在经各方当事人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该“补充协议”具有证据效力,可以成为一、二审法院处理本案遗产的重要依据。
责任编辑按: 根据本案事实,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口头遗嘱是否成立。但本案涉及的口头遗嘱似有两份:一份为被继承人汪随义在去世前三天当其同事面所说的四点遗言;另一份为原告之一唐X当众人面转述的被继承人汪随义对其所作的遗产处理的意思表示。两原告据以主张权利的当属后一份遗嘱,被告汪X所持异议的也当属后一份遗嘱。
从前一份口头遗嘱的内容和形式要件来看,汪随义在病危情况下当其所在学校的领导和同事的面对其后事作出交待,符合“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的条件,且在场的多个见证人可以说都符合见证人的条件,因此,汪随义的该口头遗嘱是成立的。但该口头遗嘱几乎并未涉及其遗产的处理问题,除“死后交一年党费”可算作涉及部分遗产处理以外,“其他事情已告诉唐X,由唐X告诉你们”,似乎是遗产处理的交待。但其告诉了唐X什么事情,汪随义并未向在场众人说明,在场众人也无法证明汪随义向唐X交待的内容。因此,即便认定该口头遗嘱有效成立,它也是和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几乎是没有任何实质性联系的。
而后一份口头遗嘱,是唐X赶来医院后在病房外向众人所作的转述,其内容就是遗产的处理。但是,该内容是汪随义何时向唐X所作的交待,在何处所作的交待,当时见证人还有谁,均无案件认定的事实交待;而唐X是该口头遗嘱中的受遗赠人,是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的;听取唐X转述的在场人无论有多少,所能证明的无非是唐X转述的内容,并不能证明汪随义作出有这样的遗嘱的证明。要证明唐X所转述的汪随义的交待,必须是在汪随义在向唐X交待这些内容时在场的人,且必须要求有除唐X以外的两个以上符合条件的遗嘱见证人作证,才能认定该内容为汪随义的口头遗嘱内容。否则,不论该内容如何合情合理,都是不能作为口头遗嘱来认定的,更不能以唐X转述时在场人未提出异议为理由来认定该口头遗嘱成立。应该认为,被告汪X在答辩和上诉中所提出的口头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是无效的,指的就是唐X转述的口头遗嘱。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前一份口头遗嘱中没有后一份口头遗嘱的具体内容,前一份口头遗嘱不能起到证明后一份口头遗嘱的内容的作用,就与本案无关;唐X因是受遗赠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其转述的内容在法律上不能被认定为是口头遗嘱的内容,因而其也不能作为证人来证明该口头遗嘱的内容;听取唐X转述的人,并未亲自在场听见汪随义对唐X所交待的内容,他们不能以遗嘱见证人的身份来证明遗嘱的内容,他们所作的证言仅仅是听唐X本人所说,属传闻证言,是不可采信的。故应认为被告的主张是有道理的。所以,本案认定口头遗嘱有效成立,欠缺直接证据的支持。
责编:youg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