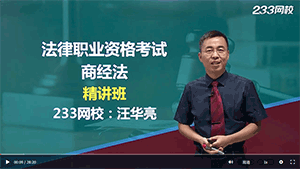周旺生谈中国法理学的若干迷点
第三个问题,法学同法律生活怎能如此疏离?法学同生活应当有紧密的关联,这是我最近几年经常谈到的。这种关联是由法学的性质内在地规定的,因为法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法学研究的对象(亦即法和法律制度等)本身就是一定范围的社会生活的制度性表述和制度性积淀。关于这一点,我在一篇短文和一篇长文中都有一定的阐述,有兴趣者可以从中了解我在这一问题上的一些观点。法学是经世致用的学问,同生活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本来似乎是无需论证的,然而在我们这里,事实上仍然需要花大力气和费大口舌才可能让一些人明白这一点。君不闻有学者就认为,“法理学还是离生活远一点好”,“法哲学就是要远离实际生活嘛”。不仅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干的。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样两种情形:一是不少学人长年疏于参与法律实际生活,对法律实践不感兴趣,他们喜欢并长于研究和撰述离生活很远的但很“新”的很“学问”的很“吸引人”的很“文化”的主题。有的人喜好把门窗关起来,甚至大白天也把窗帘拉上,开着台灯猛抽烟。本来智商就比较高,又是处于这种特定情境之下,还能不犯糊涂,还能没有激情没有思想?他想啊想啊,终于想出了一个“新的理念”、“新的主义”、“新的套路”。来源:考试大
然后写呀写呀,终于写出了很有“思想”、“观点”的文章。他用这文章振臂一呼,就吸引了学界的广泛注意力,大家跟着这个“新潮”,在这个城市和那个城市热烈“研讨”,于是差不多全国就形成了一个新热。然而就在大家特别是那些“二把刀”陶醉于这个新热之中,并且忙碌得满头大汗时,他老人家已经开始在灯下猛抽第二根烟,准备作新一轮的振臂一呼工作了。会议刚结束,他又一篇闪耀着“思想光辉”的“文章”就面世了,于是学界的众生们接着开会,“与时俱进”地赶赴“新的热点”了。这种现象在中国已持续二十多年了。二是法学同生活相疏离的情形,也表现在“文人现象”日渐彰显方面。这里所谓文人,就是差不多任何事情他都能插上嘴,都喜欢插嘴,甚至对相关问题还能“滔滔不绝”,但是要让他做任何具体的学问就不行了。这种“文人现象”,也就是当年瞿秋白所描写并告诫人们警惕滋生的现象。瞿秋白引清代一位汉学家的话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所谓“文人”正是无用之人,这是吟风弄月的“名士”,或者说简单些是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得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智识。正因为他对于当代学术水平以上的各种学问都有少许的常识,所以他自以为是学术界的人,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和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对学术是不会有什么贡献的。假使你是一个医生,或是工程师,化学技师,真正的作家,你自己会感觉到每天生活的价值,你能够创造或修补点什么,只要你愿意。就算你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罢,你可以做错误,但是也会纠正错误。你可以坚持你的错误,但是也会认真的为着自己的见解去斗争,去实行。只有文人就没有希望了,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瞿秋白所告诫人们警惕滋生的现象,不幸在今天我们的学界,正在滋生着。法学同生活相疏离的情形,当然还有其他种种表现,而喜好“倒勾”,则可以说是其中的又一种典型的“范式”。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不少学者和学生,在研究和学习中,不大注意基本问题、基础问题和常规问题,不喜欢练习基本功,而总是喜好猎奇,喜好搞“不同凡响”。你要问他一位中国的有影响的学者或法律人,比如问他张友渔是谁,有什么特点?或是问他中国的法官这些年来主要都是根据哪些法律办理案件,中国的四百多个法律究竟在事实上被法官们适合过多少个,换言之,中国的法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司法化?像这样一类的现实的他不应当不知道的问题,他是难以作答的,甚至全然无知的,更不消说指望他就这样的问题说出子丑寅卯来。而且他也可能是不屑于知道。但是你要同他谈起外国比如美国某个学者、某项宪法规定,或是希腊某圣人的某一言论,他很可能是脸上绽放出幸福的表情,同你说个不停,尽管他很可能是一知半解,但他对自己的说法却总是颇有“信心”。这种状况是不健康的,这也是法学同生活相疏离的一种表现。这样的学者和学生,不注意不关切更不去研究现实生活中的基本的实在的法律问题,而总是喜好那些又远又古又怪又奇的很“酷”的问题。他们在法学研究和学习生活中的喜好和习惯,就相当于一个足球运动员在足球比赛中不喜欢常规的战略战术,而只是喜欢搞“倒勾”和摆“倒勾”动作一样。足球比赛中的倒勾,的确是一种比较尖端和比较“酷”的战术动作,并且这种倒勾有时的确能够致敌于死地。但倒勾技术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派上用场的,一个球员不能一上足球场就往地上一躺,实施倒勾,因为实施倒勾是需要具备种种条件的,是需要特定的时空语境的。一个球队和球员,可以运用倒勾的技术在具备实施倒勾的时机致敌于死地,但不能就指望倒勾过日子。
常规的和全面的攻防战略和战术,才是取胜的更加靠得住的途径。看来,在法学的学术研究和学习方面,从只着迷于“倒勾”,转变为以常规的战略战术为基本途径,再辅之以包括“倒勾”之类在内的战术之途,应当是只喜好“倒勾”者的无法规避的选择。 第四个问题:把制定法说成有广狭之分不是误人子弟吗?法是以一种制度形态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法的基本任务是保障社会主体一定的权利和规范社会主体一定的行为,因而它应当有其较为确定的范围。法有较为确定的范围,才能让人们分清什么是法和什么不是法,才能让立法者明了应当立什么和不应当立什么,才能让司法者懂得应当以什么作为办案根据和不应当以什么作为办案根据。进而言之,只有明辨法的范围,人们才有可能真正做到依法办事,真正做到依法行使和保障法定权利,真正做到依法履行和兑现法定义务。所谓以法律为准绳之类的原则和要求也才真正具有实在性和现实性。所以,法的范围问题是法学尤其是法理学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法学和法学家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探明和讲清楚法的范围,而对法的范围的认识和理解达到何种程度,对法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认识和理解也就相应地处于何种境况。法的范围不清楚,则法学的范围就自然成问题。我在前面说过,奥斯汀在法学方面的最主要贡献之一,也正在于他第一个系统、集中而明确地阐明了法的范围问题。然而在我们的学界,这个问题迄今还是阻碍我们的学术,首先是阻碍法理学走向科学的一道关口,存在着种种迷点。这些年来,在学界广为人知的一些有关法的范围问题的“理论”,就堪称严重误人子弟。有关法的范围问题的误人子弟的迷点之一,就是影响甚大的所谓广义的法和狭义的法的“理论”。二十多年来,在中国研究和学习法学的人,恐怕没有人不知道所谓广义的法和狭义的法这种说法的。而且这种说法似乎是深得人心的,全国绝大多数法理学教科书对法的概念的界说,都是使用广义的法和狭义的法这种说法。这种说法的表述虽然并不完全一致,但其基本内容则是一致的。特别是其中这样的表述尤其误人子弟:法有广义的法和狭义的法之分,广义的法指各种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狭义的法则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这种说法所以误人子弟,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它一走进实际生活,马上就碰壁。我还记得,二十年前,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一位很有影响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他是广义论和狭义论这种说法的阐述者和持有者,而我觉得法作为指引和规制社会主体行为的社会规范,作为法律人据以行为的制度根据,是应当有其较为确定的范围,而不宜采用广义论和狭义论这样的形是而实非的说法的。当时我举了这样的例子说:假如我是法官,在开庭审理案件时,我能说我是广义论持有者,所有国家机关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都是法,我都拿它们作为办案根据吗?或者我能说我是狭义论持有者,我只承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是法,只拿它们作为办案根据,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我都不买账吗?再或者,我能说我一忽儿是广义论持有者,一忽儿是狭义论持有者,到底什么是法,什么是办案的根据,由我看情况办吗?我当然不能这样说。所以说,广义论和狭义论在书本上讲讲,人们未必能够马上看出它的毛病,但一到法律实际生活中,它就说不通,更是行不通了。
但那位老先生说:西方也有广义和狭义的说法,并且进而责道:“那你看,到底应当怎么说?”在师道有权威的文化传统之下,我感到语塞。我当时就想回应但却不适宜这样回应:这是对西方人的误解。西方人的确也讲广义的法和狭义的法,但人家所说的广义的法,主要指的是理性法或自然法,人家所说的狭义的法,主要指的是人定法。而我们现在把后者(亦即作为制度范畴的法)又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不仅行不通,也是对西方人的误读。我只得苦涩地戏言曰:“倒也是,法这种东西多么复杂,谁能讲清它的范围?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遗憾的是,多少年过去了,广义论和狭义论仍然没有退出学术的境域,仍然是中国法理学一个基础性观点,仍然从负面影响中国法学的发展,也从负面影响法律实际生活,使本来法盲就非常之多的社会主体,不能有效地辨明中国的法到底有多大范围。 第五个问题:法的渊源和法的形式没有界分吗?法的范围混沌不清也表现在法的渊源和法的形式不分方面。我在前面谈到奥斯汀在明确法的范围方面所作的努力,他的这一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厘清法的渊源和法的形式界限的努力。今年我就法的渊源和法的形式问题已经写了几篇文章,其中一篇的题目就叫做“法的渊源与法的形式的界分”。我的文章的大意是说:奥斯汀以来的法律学人,虽然试图在法的渊源和法的形式之间踩出清晰的路径,却终未获取如意的结局。迄今无论英美还是欧陆抑或中国学界,仍然普遍混淆两者的界限,以致把不是法的东西视为法,把未然的法和已然的法、可能的法和正式的法混为一谈,在法律生活中就是经常淡化法和非法的边界并由此脱离法治原则。而且,历来法学流派的分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表现在对法的渊源和法的形式取不同态度方面,分析法学所讲的法实际就是具有法的形式的法,而自然法学、历史法学、社会法学所讲的法则更多是尚未形成法的法的渊源。然而法的渊源和法的形式的确是不容混淆的:法的渊源是法得以形成的资源、进路和动因,是法的半成品和预备库,是未然的和可能的概念,是多元化地存在着的,它更多是社会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法的形式则是提取和升华法的渊源的实际成果,是法的既成产品,是已然法和正式法的不同表现形式,是以国家权力体系为主线贯串在一起的,它更多地凝结了一国现实的政治和法律体制。它们本是两种事物,内涵两种价值,代表法的形成过程中两个不同阶段和表现形态。混淆法的渊源和法的形式界限的观点,突出地表现在混淆习惯和习惯法、判例和判例法之类的界限方面。很多人所说的习惯法,实际上就是习惯;很多人所说的判例法,其实就是判例。甚至在2002年巴黎的一次研讨法的渊源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我注意到外国学者中也有一些人对这种界限不得要领。我当时作了一个即席发言,强调了习惯、判例、道德、政策、乡规民约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东西,都是法的渊源,而习惯法、判例法则同宪法、法律、法规等等一样,属于法的形式。像习惯、判例之类的法的渊源要成为习惯法、判例法,亦即成为法的形式,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之一:或是为国家立法机关所采纳,在有关法律、法规中加以认可,如中国的1950年婚姻法关于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问题从习惯之类的规定即是;或是为国家司法机关所选择,在有关司法判决中加以援用,如英美法系的实际情形。未经这类程序,习惯就是习惯而不是习惯法,判例也就是判例而不是判例法。这样的观点,我在近年的有关文章中已有阐述。我希望我们的年轻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们,能在基本功上多下功夫,避免出现这样的毛病:成天所讲的一些观点,所学所掌握的,有相当大的成分,原来不过是似是而非的东西,然而自己却还不知道,还以为掌握了多少宝贝,还以为自己已经了不得。 第六个问题:法律真的就是正义的体现?法,说到底,是对实际生活的有选择的制度性表述,它首先要同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相吻合,同时,这种表述是由人来进行的,这就不能不带上表述者的主观的愿望。这样,法就必然地表现为:它是实然和应然的混合,在比较好的情况下,则是实然和应然的有机统一。
这种情形在法学上,就表现为法的概念实际上是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其一,法是什么?其二,什么是法?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就是真实的法与理想的法的问题,或者说就是实然的法与应然的法的问题。法是什么的问题,就是认识和解说实际生活中真实的法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由于实际生活中的法非常复杂而比较难以回答,但总是可以给出一个明确、具体、甚至科学的答案。因为这种法是真实的,是可以看得见的,是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直接关联的。什么是法的问题,就是探索和描绘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生重要作用的法,应当是什么模样的问题。由于这种法虽然源于实际生活但却不同于实际生活或高于实际生活,甚至与实际生活所能接受的状况差之颇远,因而人们难以对这种法给出一个大家都能认同的定义。应然的法,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在具有不同价值观、对法寄予不同希望的人们那里,是难有一个共通的定义的。
责编:yougu
相关阅读
-
2008年司法考试辅导:法的价值专题讲解
-
司考指导:顺利通关司法考试法理学复习必背
-
司法考试答疑之法理学中法的要素?
-
司法考试答疑之判例法都是不成文法吗?
-
周旺生-考点和习题精解(三)
-
周旺生-考点和习题精解(四)
-
周旺生-考点和习题精解(五)
-
司法考试:周旺生-考点和习题精解(二)
-
司法考试:周旺生-考点和习题精解(一)
-
司法考试:关于我国法理学上认可的分类答疑
-
司法考试答疑之哪些属于社会法?
-
查士丁尼法典是法典编纂、汇编还是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