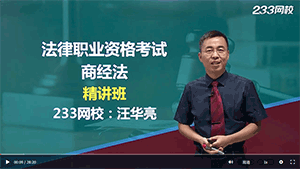但在法治社会的刑法当中,我们采用的是罪刑法定原则而绝对的排斥类推,严格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要求法官严格按照法律的明文规定来定罪处刑。由此可见,“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两者的机能是正好相反的。“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开放的机能,使民法典成为一个相对开放的规范性体系;而“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具有限制的机能,它使刑法典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规范性体系。为什么两个基本原则在两个法律部门当中具有如此相反的机能?我认为主要由民法和刑法这两个部门法不同的性质所决定。因为民法主要解决民事纠纷,而民事纠纷是平等主体的纠纷。公民与公民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或公民与法人之间是平等的主体,他们之间发生了纠纷,起诉到法院,要求法官做出公正的裁断。在民事审判当中,法官具有更为超然的地位,因此,民法典虽然为法官审理案件提供了大多数明确的法律根据。但由于民事纠纷的复杂性,不可能在民法中都规定下来,就赋予了法官根据诚实信用的法律基本原则来审理那些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案件。但是,在刑法中,刑法是规定犯罪和刑罚的,一个公民的行为一旦被确定为犯罪,就会受到相应的刑罚处罚,轻则剥夺权利、财产,重则剥夺自由、生命,刑法关系到一个公民的生杀予夺。而犯罪本身涉及到国家和公民个人的纠纷,按马克思的说法,是孤立个人反抗统治关系的一种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有效地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就需要通过罪刑法定原则来严格限制国家的刑罚权。因此,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上是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个人权利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对于国家来说,尤其对于国家的司法机关来说,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来认定犯罪和处罚犯罪,而不得超越法律的规定。对公民个人来说,只有当他的行为触犯了刑法、构成了犯罪,才应当受到法律追究,如果他的行为没有触犯刑法,不够成犯罪,就不会受到法律追究。因此,罪行法定原则在国家的刑罚权和公民个人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它使得刑法具有某种契约性,是国家和公民个人之间双方的一种约定,一种协议。也就是国家司法机关允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来认定犯罪和惩治犯罪。因此,这种刑法规范具有双重机能。一方面是裁判的机能。所谓“裁判性能”,是法官定罪量刑的裁判活动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在这个意义上说,刑法本身具有严格限制司法权的性能。另一方面,刑法又是一种行为规范,它告诉公民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哪些行为被定为犯罪,受到何种处罚。所以,它具有行为规范的功能。这样的刑法的契约性,使得它具有某种正当性,具有某种限制性。这种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刑法,也就是法治社会的刑法区别于专制社会刑法的一个根本特征。在专制的社会里也有刑法,甚至它更为完备和完善。但是在专制社会里,刑法是国家单方面镇压犯罪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刑法本身并不具有对专制权利的限制功能,对专制权利它是没有限制的,它主要是用来镇压犯罪,是镇压犯罪的一种工具。只有在法治社会里,刑法具有一种契约性,这种契约性就是通过“罪刑法定”来获得。应该说,“罪刑法定”和“类推”两者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罪刑法定”是绝对排斥“类推”的。在“罪刑法定”的情况下,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就是看法律是否有明文规定。而在类推的情况下,犯罪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另一部分是法律虽没有明文规定,但可以通过类推定罪。由此可见类推所确定的犯罪的范围比罪刑法定原则下犯罪的范围更要宽泛一些。类推一旦被滥用,就可以侵犯到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它是被罪刑法定原则所绝对禁止的。由此可见,罪刑法定原则是法治社会刑法的内在精神。
而我国在1979年的刑法中没有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而是在第七十九条规定了类推制度。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因此,1997年刑法在修订的时候,就废除了1979年刑法关于类推的规定,在刑法第三条明确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我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确立,是我国刑法在民主与法治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确定的重要意义,我认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分。当然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中的确立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在刑法中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我们国家就实现了罪刑法定。如果不想使罪刑法定原则成为法律口号或成为法律标语,我们在司法活动中就必须要切实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所以,这里有一个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我们现在应当致力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在某种意义上说,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甚至比立法化更为重要,如果没有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罪刑法定原则即使在刑法中规定下来,也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纸空文。
罪刑法定原则带来了刑事司法理念的一些重要变化。过去的刑事司法理念是建立在专政的基础上的,往往把刑法看作是惩治犯罪的一种专政工具,强调通过惩治犯罪来保护社会利益,保护人民利益,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护。正是在这种专政的司法理念下,我们强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把社会危害性看作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一个行为之所以被立法者规定为犯罪,是因为这个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一个行为之所以被司法者认定为犯罪,也是因为这个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在那些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只要这个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就可以通过类推的方法来定罪处刑。因此,社会危害性理论也为类推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我们认为社会危害性的理论,实际上是实质合理性的司法理念,对一个问题做实质合理性的判断。而罪刑法定原则它所倡导的恰恰是形式合理性的司法理念。在罪刑法定的原则下判断一个行为罪与非罪的唯一标准就是要看法律是否有明文规定。如果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即使这个行为具有再大的危害性,也不能按照犯罪来处理。这是罪刑法定原则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因此,罪刑法定原则所倡导的形式合理性和社会危害理论所包含的实质合理性之间是存在矛盾和冲突的。
那么基于形式法治这样的理论,面对这种矛盾和冲突,我认为我们应该选择形式合理性而非实质合理性。根据这种“形式合理性”的观念来认定犯罪和惩治犯罪,必然意味着某些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在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犯罪行为不能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在这种情况下,在“实质合理性”方面就会有所丧失,也就是说,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必然会带来某种实质合理性的丧失,它是有一定的代价的。对于罪刑法定原则带来的可能丧失实质合理性的代价,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那我们的社会必须要逐渐地提高这种承受代价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才是可行的。当然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同时也对我们的整个刑事司法制度乃至我们的司法制度、审判制度本身提出了一种要求,也就是要求司法独立。可以说,司法独立也是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一个基本逻辑前提。只有司法独立、法官独立,法官才有可能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惩治犯罪。那么在司法不独立的体制下,行政机关以及其他部门可以随意干涉法院定罪量刑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是无从谈起的。现在我们的司法独立还是远远没有做到的。很多案件都是有一些领导的批示,这些领导批示和法律规定之间往往存在着直接的矛盾。比如有些案件领导批示了一定要严惩,但这种行为在刑法中没有规定为犯罪,严格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就不能被处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法官、司法机关就面临着重大的考验。是屈从于领导的批示、违反罪刑法定,还是坚持罪刑法定、而完全把领导批示放在一边。应该说在目前的环境下,要完全把领导的批示置之不顾,应当说是有很大困难的,甚至有很大风险的。在这种情况下,罪刑法定司法化是十分艰难的。
另外,罪刑法定司法化对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提出了很高要求。因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关键看法律是否有明文规定。这里就有一个如何理解法律规定的问题。如何理解法律规定的问题,实际是一个找法活动,法律规定本身等着你去寻找,它本身并不是翻在那儿等着你去适用。在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过程中,“找法”的活动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你不能正确的找到法律,比如说,某一行为,本来法律有明文规定,但没有找到这个法律规定,而误认为法律没有规定,因而没作犯罪处理,这显然是放纵了犯罪;而另外一行为,法律本来是没有明文规定的,但找错了法律规定,而误认为法律有明文规定,这就会冤枉无辜。因此如何找到法律规定是罪刑法定司法化的一个基本前提。
法律规定本身是相当复杂的。从理论上看,法律规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法律的显形规定,另一种是法律的隐形规定。在法律规定是显形的情况下,根据法律的字面含义,就可以得出法律是否有明文规定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寻找法律规定是比较简单的。在法律是隐形的情况下,如果光看法律的字面,并不能得出法律是否有明文规定的结论,而是要对法律规定的内容进行逻辑的分析,要对相关的法律规定,来进行相互之间的一种判断,甚至要对立法精神,来进行深入探究。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来确定某一行为是否有法律明文规定。
这里举一例来说明找法活动的艰难性。某地曾经发生过这样一起案件,有一公民从香港乘飞机入境,随身携带了10多公斤黄金,没有报关,后案发。这是一个走私黄金入境的行为,对这一行为是否能按照犯罪来处理,关键看法律是否有明文规定。根据这样的事实来寻找法律规定。由于这是一种走私行为,我们就需要到有关走私罪的行为中寻找。我国刑法第151条第2款,有一个“走私贵重金属罪”,在“走私贵重金属罪”中包含黄金,但我们看第151条第2款就会发现,“走私贵重金属罪”是指走私黄金白银出口行为,明确讲是走私出口,而没有包括走私入口,而且这里规定“走私出口”才可以构成“走私贵重金属罪”,并不是立法的疏漏。因为在同一条款中,对于其他某些物品,比如说文物,它明确规定走私进出境的,包括入境、出境,都可以构成走私罪。如果仅根据这样一个结论,我们似乎就可以得出结论,刑法只规定了走私黄金出口的行为构成犯罪,而未规定走私黄金入口行为构成犯罪。因此,这种行为不能按犯罪来处理。如果由此而得出这样结论,还是比较草率的。因为我们光是考察了刑法显形的规定。从刑法显形的规定来说,确实没有包括这种行为。那么这种行为能否包含在法律的隐形规定中呢,我们还要继续找法。我们来看刑法第153条,“走私普通货物品罪”,那么黄金能不能包含在普通货物品中呢?根据刑法153条规定,所谓“走私普通货物品罪”是指走私刑法第151条、152条、347条规定以外的货物品。有的人会说这里的普通货物品是指刑法第151条、152条、347条规定以外的货物品,而黄金在151条就有规定了,因此就不能包含在普通物品罪当中。这样的理解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认为这样的规定完全可以做另一种理解,这种理解是指刑法第151条,152条,347条以外的货物品,我们把“规定以外”理解为被刑法第151条,152条,347条规定为犯罪以外的货物品,比如像走私黄金出口已经被刑法第151第2款规定为犯罪,当然不能再包含在普通货物品当中来。但是“走私货物品进口”的行为并没有被151条规定为犯罪,所以可以包含在走私普通物品罪当中来。光是从语言逻辑上说,并不能把这种情况排除在外。那么我们再考察走私黄金进口行为,到底能不能包含在153条“走私普通货物品罪”当中,需要对走私罪的立法精神进行考察。实际上海关监管的这种物品有两种:一种是国家禁止进出境的物品,是一种违禁品,指毒品、淫秽物品、武器弹药、核材料等等。这些物品是国家是禁止进出境的;而另外一种是国家允许进出境的,但这种进出境需要缴纳关税。因此这两种物品在海关监管中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刑法对这两种不同物品分别规定了不同的走私行为。前一种走私行为,它所破坏的主要是海关监管;而另一种走私普通物品的走私罪,它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通过逃避海关监管而脱逃关税。因此,刑法第153条“走私普通货物品罪”是根据脱逃关税的数额来作为定罪处罚的标准的。那么一种物品一般来说,要么是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物品,要么是国家允许进出口的物品。因此走私这两种物品可以根据不同走私罪来定,但黄金恰恰是一个例外。黄金的特点是国家禁止出口,但允许进口。就出口而言,国家是禁止的,只要是走私出口,就构成了走私贵重金属罪。但对于黄金,国家是允许进口的,但如果进口,必须要缴纳关税。而这种走私黄金进口的行为,恰恰是逃脱了关税。因此,对这种行为,按走私普通货物品罪来定罪,完全符合立法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