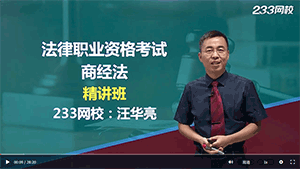以上通过一个“走私黄金进口行为”找法的过程来作这一分析,可以看出,在罪刑法定司法化的过程中,对法官素质提出的要求是很高的。如果法官缺乏对法律深刻的了解,缺乏法律的基础知识,很难胜任法官的职责,罪刑法定司法化也就不可能实现。当然,我们说罪刑法定司法化在不同国家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在有些国家这种程度高一些,在有些国家要低一些。这是由不同国家不同的国情所决定。也就是一个国家罪刑法定原则到底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接受程度,取决于一个社会法治文明程度。
比如说我们举两个外国的例子,可以看出在外国它实行罪刑法定的程度。一个是法国的例子。法国刑法典中规定了脱逃罪,但它所规定的脱逃罪明确列举了三种方法,采用攀墙、掘洞、蒙混的方法脱逃的,构成脱逃罪。这三种方法,一般来说,包含了所有的脱逃行为。但是在80年代中期,法国出现了一个脱逃的例子,行为人所采取的脱逃方法恰恰超出了法律所列举的这三种方法。它是监狱内的犯罪分子与监狱外的人员相勾结,有一天乘监狱内所有的囚犯在操场上放风,这时从监狱上空飞来一架直升飞机,直升飞机挂下来绳梯将犯人接走。对这个案件作出无罪的判决。另一案件是英国的案件。英国的制定法中规定了在皇家飞机场跑道附近扰乱飞行秩序的构成犯罪。现在一个被告人,它不是在飞机场的跑道附近,而是在飞机场的中间扰乱飞行秩序。那么在定罪时被告人被判无罪,有时候是很难接受的。但是为什么要实行这么严格的罪刑法定,要把法官定罪严格限制在法律范围内。在刚才所讲的两个例子中,实际上却属于法律规定有漏洞。那么对于法律规定漏洞所产生的后果能不能要求被告人来承担,是由被告人承担还是立法者、社会来承担?显然他们认为法律的漏洞所产生的不利后果不应由被告人来承担。因此对被告认作无罪判决。那么在这两个案件中,被告人行为显然是危害社会的,是应当作为犯罪来审判的,仅仅因为没有被法律的文件所包含就作出无罪判决。他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决,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个案件中,法官超出法律的有罪判决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允许法官超出法律规定作出有罪判决,那么不能保证法官在每个判决中都是正确的,就可能出现法官超出法律规定将一种没有危害性的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理,从而就会滥用司法权力,就会侵犯公民的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因此他们要求对法官的裁量权进行严格限制。这样一种做法从个案来说使之合理性有所丧失。但是从整个国家的法制建设来说是有利的,有利于从根本上保证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因此他们从这种观点来平衡利弊。这样的选择在我们国家比较困难。
前一段时间黑哨事件有关人员被抓了,能不能作为犯罪人来处理,是不是刑法中有明文规定。那么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严格来说在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刑法中有两种受贿罪,一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显然裁判不是属于公司企业人员,因此不能定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另外一种是普通受贿罪,它的主体是国家公务员。裁判员也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因此要套这两种罪都有困难。但对这种行为,它确实有极大的危害性,如果不把他作为犯罪来处理,那么就会带来很大的社会压力。如果法官严格按照法律来判,有一个社会接受能力的问题,所以这在我们国家需要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我们不可能某一天突然实现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因此我们要推进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只有这样才能提升我们国家的刑事司法水平。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的关系。它们中都有一个关键词“真实”。对真实的追求是人类永恒的冲突。在司法活动中,人们也往往把真实当作最高境界来追求。即使在古代社会实行神明裁判的情况下,也是在追求真实。只不过是在追求他们那个时代能够达到的真实。随着科学的发达,可以凭借科学得手段来追求真实。因此几千年历史的发展,追求真实的手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追求真实的信念始终没有变化。在司法活动中得到的真实到底是法律的真实还是客观的真实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里面首先有一个人的认识能力问题。关于认识能力问题,恩格斯说:“人的思维是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统一。”人的思维至上性和非至上性都是有条件的。当认识的主体是个体的人由于受到主观的局限性,思维具有非至上性。当认识的主体是人类的时候人的思维具有至上性。当这种认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认识活动时,这种认识由于受到客观局限性,那么它是非至上的。但是当把人的认识放到认识的历史长河中,人的认识具有之上性。因此你现在不能认识,一百年后能认识,一千年、一万年以后总有一天能认识。人的认识是一种生生不息、永无止境的过程,人们总有一天能够到对绝对真理的认识。恩格斯的论断与不可知论划清了界线,坚持了可知论观点,一切事物可知,人们能够达到至上性认识。另一方面,可知是有条件的。可知不意味着任何情况下都能实现。在司法活动中同样包含着人的认识论。司法活动中一事件到底是至上的还是非至上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决定:人类司法活动本身具有非至上性,而不具有至上性。第一原因是司法活动参与者都是个体的人,法官、检察官、律师都是个体的人,由于受到主观局限,不能完全客观地达到认识。第二,司法活动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必须在法定时间内获得某种真实认识,这种真实认识具有非至上性。第三,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司法认识活动具有非至上性。如果我们面临一、二个案件,我们可以动用所有的资源来认识这个个别案件。可我们现在面临成千上万个案件,分配到每个案件的司法资源有限,我们也不可能完全达到对客观真实的认识。最后是司法认识活动特性决定的。从时间来说,司法认识有三种,一是对现在的认识,这种认识正在发生,比较容易;二是对将来事物的认识,对各种事物的预见,这种认识比较困难;三是对过去事物的认识,也是对历史的认识。这种情况下,认识对象发生在过去,认识发生时距认识的时候有时间的间隔。对过去发生的事物也很难认识。司法活动是对过去发生事物的认识。司法认识的特点是犯罪案件发生在前,认识过程发生在后。由于时间的推移,有些证据可能灭失了,有些证人的记忆可能淡忘了。因此通过诉讼活动,要想完全真实复原案件中的情况可能有困难。由于以上四个原因所决定,司法活动是非至上性活动。所以在司法活动中,我们所要追求的只能是一种法律真实而不是客观真实。法律真实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真实。法官只能对法律真实负责,不可能完全对客观真实负责。法官没有看见张三杀人,最后要作出判决张三不曾杀人。法官的判决只能建立在证据基础上。法官判决张三构成杀人罪,是说根据现有证据证明张三杀人。……至于张三在客观上有没有杀人那是一个客观真实。法官只能对现有证据负责,不能对证据之外的客观真实负责。这是值得研究的。在司法过程中,95%的案件能查清事实。但总有5%-10%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这些案件被称为疑难案件。其特点是既有一些有罪证据,你判无罪可能是错的;但又有一些无罪证据,判有罪可能也是错的。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面临着错判还是错放的选择。我们过去宁愿错判也不错放。错判还是错放的选择是犯一个错误还是两个错误的选择。错判是犯了两个错误,它使无罪的人受到了法律的追究,又使有罪的人逃脱了法律的追究。因此是犯了两个错误。错放只是犯了一个错误,使一个有罪的人逃脱了法律的追究。他认为,一个人当然不愿意犯错误,但是非要犯错的话,人们宁愿犯一个错误也不愿犯两个错误。所以他面临犯一个错误还是两个错误的时候,正确的答案是宁愿错放也不错判。他的论述具有启发性。但我认为在这个分析中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第一个问题,宁愿犯一个错误而不愿犯两个错误这个选择果然是这样吗?如果要这样的话必须有一个前提,这些错误大小相等。因为这些错误大小相等,两个错误加起来大于一个错误。所以人们才选择犯一个错误,而避免犯两个错误。但当这两个错误大小不相等时,人们可能宁愿犯两个错误而不犯一个错误。因为两个错误是两个小错误,一个错误是一个大错误,两个小错误加起来还不如一个大错误。因此在考虑错判还是错放的时候,不在于是一个错误还是两个错误,而在于错判还是错放两个错误哪个大哪个小。那么过去人们为什么宁愿错判而不是错放,是因为当时人们认为错判是一个小错误,是一个业务水平问题;而错放是一个大错误,是一个立场问题、思想问题。错判和错放受到的社会压力是不一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才宁愿错判而不错放。要使人们感到错判是一个大错误,侵犯了公民的自由权利,而错放只是一个小错误,是一个认识水平问题。另一个问题,错判和错放的“错”到底是一个什么标准,是以客观真实为标准还是以法律真实为标准。这种“错”实际还是以客观真实为标准。在当时情况下,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他有罪,因此你判有罪应该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下判无罪是正确的,从法律真实角度来说是正确的。之所以说是错放,指的是根据客观真实根据事后发生的客观证据证明这个案件确实是他做的。从客观真实来说,“放”是错误的,从法律真实来说,“放”是正确的。这里涉及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的逻辑结论是:需要证明的是有罪,不需要证明的是无罪。在这种所谓的错判还是错放的情况下,既然不能证明有罪,“放”就是正确的方法。这种无罪推定原则于有罪推定是矛盾的。有罪推定的逻辑结论是:不能证明无罪就是有罪。需要证明的是无罪而不需要证明的是有罪。这种错判还是错放本身就含有一种有罪推定的思想观念在里面。实际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应该是疑罪从无。因此我们在司法活动中讲的真实应当是法律真实,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真实。因为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不能将所有的案件都查清楚,关键问题是查不清楚的情况下怎么办?查不清楚的情况下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只能做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而不能要求一定要把无罪查清楚才能判无罪。所以有罪无罪在能否查清的情况下是不一样的。有罪必须查清楚,有罪需要证明,如果不能证明,就是无罪。但在司法活动中,无罪推定观念还没有树立起来。因此面临疑难案件不能查清,不能证明是有罪还是无罪,就会导致一个长期关押,甚至超期关押。这种做法和无罪推定原则相矛盾。因此我们要从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转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证公民的个人权力和自由。
最后一个问题是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问题。这涉及到程序和实体的范畴。过去把程序和实体看作一个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认为程序只是实现实体的手段。这种观念往往重实体而轻程序,甚至陷入了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非道德主义范畴。我们现在需要重新认识程序和实体的关系,也就是说程序有没有独立于实体的价值。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程序正义进行了研究。程序正义有三种,第一种是纯粹的程序正义,只要程序是正义的,实体必然正义。因此程序正义决定实质正义。纯粹的程序正义指的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抓阄、赌博等。抓阄情况下,程序是公正的,实体一定公正。第二种是完善的程序正义。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有两个不同的标准,但是通过设计程序能够完全实现实质正义。罗尔斯举例:分蛋糕时,一个蛋糕两个人分,怎样分得公平呢?切蛋糕的人后拿蛋糕能使分蛋糕公平。为了使自己分得的蛋糕与他人一样大,必须保持分蛋糕公平,因此能做到实际处理结果的公平。如果程序相反,切蛋糕的人先拿蛋糕那么可能会把蛋糕切得一大一小,失去公平。由此可见程序的设计对保持实体公平很有作用。第三种,不完善的实体正义。在这种情况下,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有不同标准,无论怎样设计程序也不可能得到实体正义。罗尔斯说:“审判就是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在审判中,程序正义有程序正义的标准,实体正义有实体正义的标准。在审判中,实体正义的标准是定罪量刑是否正确;而程序正义的标准是诉讼程序是否符合标准。但是在刑事审判中,如果完全遵守诉讼程序并不能保证实体处理结果就一定公正,也就是说你如果严格遵守程序也可能会出错。但反过来说,你违反程序,实体处理结果可能是正确的。因此在刑事审判中,面临着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冲突时,两者往往发生这种冲突,那么面临这种冲突到底是选择程序正义还是实体正义?我认为,在刑事司法理念中,我们应当建立起一种程序优先的观点,应当把程序正义放在实体正义之先,主要是由两种正义的特征决定的。一般来说,程序正义的正义标准具有客观性、明确性。相对来说,实体正义的标准具有模糊性,主观感受性。那么,在刑事审判当中就量刑而言,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你很难说多判一年就错,少判一年就对,它有一定的裁量余地。即使是定罪这个问题,也并非像1+1=2这么简单。那么有些案件就界于有罪和无罪之间,你很难说判无罪就一定错,判有罪就一定对。正式由于这两种不同的正义标准的特征所决定的。我们认为,应当把程序正义放在实体正义之先的位置上。程序正义本身具有很大的功能,他有一种吸收不满的功能。在纯粹的程序正义的情况下,抓阄我们没有抓到这个东西,我们当然不乐意,我们实际还想抓到这个东西。他有这个不满,但抓阄这个程序是公正的,因此他的不满就被程序正义所吸收。所以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手气不好。
在完善的程序正义中,你切蛋糕,尽管你努力的想把蛋糕切的一样大,但是蛋糕还是有大有小,结果还是有可能大的被别人拿走,你剩下的一块小一点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尽管不乐意,想取得一块和别人一样大的蛋糕,但是,你的不满也被吸收了。因为这个蛋糕就是你自己切的。谁让你不能把蛋糕切的一样大?程序正义有吸收不满的功能。如果一个案件的审判是公正的,但是程序不公正就会制造当事人不满。使他对于一个本来公正的处理结果也不能接受。我们讲司法公正其中当然包含程序的公正和实体公正,我们是既要得到实体公正有要得到程序公正。但我们认为在司法实践当中,首要的还是程序公正。没有程序公正就谈不上司法公正,这一点很重要。
前两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学习“三个代表”理论中提出一个口号:人民法院的工作要做到使全体人民都满意。因为人民法院代表人民,所以你要做到你的审判工作使全体人民都满意。结果,我们有一个教授对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报告提出了批评,说法院的审判工作不可能使全体人民都满意,只能做到50%的人民满意。因为民事案件有被告和原告,那么你判原告胜,那么原告满意被告不满意。判原告败诉,则被告满意,原告不满意。刑事案件有辩方和控方,判任何一方胜,另一方就会不满意。你的处理结果只能使一半的人满意,不可能使双方都满意。我们认为这个说法仅就实体正义而言。从程序公正的角度来说,人民法院不仅能做到而且应当做到使全体人民都满意,也就是说在审判程序当中,能够引入双方当事人参加,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那么使实际处理结果是从这样一个程序中的出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一方当事人对处理结果不满意,那么他也能接受。这就是程序公正的重要功能。
比如说,前几年在美国审理了辛普森案件,媒体调查有70%-80%的美国人认为判辛普森无罪是不能接受的都认为他就是杀人犯,但是当你进一步问美国人辛普森是不是受到了公正的审判,几乎每个美国人都会说辛普森确实受到了公正的审判。这里所谓公正的审判是指审判辛普森的程序是公正的。由这样的一个公正的程序的出的大家都认为是错误的结论,但是大家也都能接受,程序的公正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可以说程序的公正主要是保护被告的,就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而言,几千年过去了,实体规则变化不大,两千多年前刘邦如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样一个刑法规则。现在刑法里面同样坚持这一规则。但是程序规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换,那么在一个法制社会里体现对被告人,对犯罪人的权利保护的主要是程序正义。
有有一个美国人曾说:“如果要做这样一个选择,采用苏联的实体法和美国的程序法来审判”他宁愿接受前者,因为苏联的可能是比较糟糕的。也就是说程序和实体比较可能程序更重要。因此,尽管苏联的刑法是很严酷的,但如果你采用苏联这种很严酷的刑法而采用有利于被告人的程序法,他宁愿选择苏联这个法律来接受审判。所以程序公正是非常重要的。
那为什么要强调对被告人和犯罪人的权利保护呢?我们认为一个社会的法制文明很大程度上法律对被告人、犯罪人的利益保护程度。看一个国家的法制文明程度你不要去看他这个社会里面守法的公民权利是如何受法律保护的,关键是看被告人的权利是不是受到了法律的保护,如果在一个社会里犯罪的人都能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没有犯罪的公民他们受到的法律的保护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们要强调通过程序来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一点很重要。
当然,程序正义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体制问题。我么现在的刑事司法体制是公检法互相配合的一种司法体制,那么在这样一种司法体制下,构建了一条司法流水线。公检法是流水线上的三道工序。而被告人只是一个消极的客体。我们认为这种司法体制不利于有效地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现在有这样一句俗话来反应这种流水式的定罪方法,往往说公安式做饭的,检察院是端饭的,法院是吃饭的,有的人还加上一句,律师是要饭的。所以,是以侦察为中心的公安是老大,是一种侦察中心主义的诉讼模式。这种模式当然是有利于惩治犯罪,但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然而,实际上,公安式做饭的,检察院是端饭的,法院是吃饭的并没有错。关键是做饭的决定吃饭的还是吃饭的决定做饭的。我们现在的体制是做饭的决定吃饭的,我做什么你就吃什么。要改变为吃饭的决定做饭的,我吃什么,你就做什么饭端什么饭。也就是构建一种以审判为中心的体制。要使控辨双方的法律地位平等,法官居中裁判,由法官根据法律规定来确定一个人是有罪还是无罪。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套刑事审判中的正义。从而有效地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这一点非常重要。
以上,我们就刑事司法理念中的三个问题作出了一些论述。在这一领域中,我认为重要的给大家做了些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