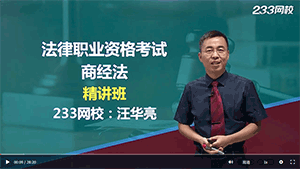第一, 关于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问题。
在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这一范畴中,涉及一个中心词-“合理性”,应该说,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法律制度都要追寻这种合理性。但是,“合理性”又可以分为形式的合理性和实质的合理性,这两种合理性是有所不同的。所谓“形式合理性”,是一种手段的合理性、客观的合理性;而“实质合理性”,是一种目的的合理性、主观的合理性。它们的性质有所不同。在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中,通常都想使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二者兼而得之。在立法的时候,主要是要在法律上将实质合理性加以确认,使实质合理性转化为法律规定,在司法活动中,按法律规定加以适用,这样就会使实质合理性转化为形式合理性。因此,在理论上来说,实质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二者应该能够得到统一。但这种统一,往往处于因然的状态。
但实质上,二者经常处于矛盾和冲突关系。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思。韦伯曾经就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关系做过十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法逻辑”,法律这种逻辑和通过法律来满足的社会实质价值要求之间存在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马克思。韦伯这里所讲的“法逻辑”,指的是法律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合理性。而他这里所讲的“通过法律来满足的社会实质价值要求”是一种实质合理性。在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那么这种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中国古人有一个十分形象的说明-“法有限,情无穷”。因此,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就表现为法的有限性和情的无穷性之间的矛盾。正因为法有限而情无穷,因此,很难用有限的法来规范无穷的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客观存在的。表现在刑法当中,所谓“法有限”,指的是法律条文有限。一部刑法典,少则二三百条,多则八九百条,条文总是有限的,那么在刑法典中,设置的罪名是有限的;但另一方面是“情无穷”,这里所谓的“情无穷”,指的是犯罪现象本身是无穷无尽的。在一部刑法典中,很难把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严重危害社会行为都毫无遗漏地规定下来。这种“法有限”和“情无穷”之间的矛盾之所以产生,我认为由以下两方面原因决定:第一, 由立法者的立法能力的有限性和犯罪现象的无穷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
社会上存在着的犯罪现象是无穷无尽的,而立法者的立法能力是有限的。在立法的时候,立法者需要对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加以理论上的概括,然后作为罪名在刑法典当中加以规定。立法者立法能力上的有限性,就决定着在制定刑法的时候,不可能把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毫无遗漏地规定下来。
第二, 由刑法的相对稳定性的要求和犯罪现象的变动不拘性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刑法本身具有稳定性的要求。尽管这是一种相对稳定性,但是这种稳定性的要求是刑法所必不可少的。刑法不能朝令夕改,它必须要保持一定时间的相对稳定性。另一方面,犯罪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变动的。这里有一个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双向运动。一方面,有些行为在刑法中规定为犯罪,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消失了,需要非犯罪化;另一方面,有些行为在立法时没有社会危害性,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产生了社会危害性,因此需要予以犯罪化。可以说,这种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永恒的过程。那么正是刑法本身的稳定性的特征和犯罪现象的变动不居性的特征的矛盾,决定在刑法中不可能包容社会上所存在的各种各样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刑法典从它制定出来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滞后于社会生活的发展,滞后于犯罪现象的发展。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所决定,刑法中所规定的犯罪,实际上只是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严重危害社会犯罪中的一部分。此时,法的有限性和情的无穷性之间的矛盾就变得十分明显。那么,如何解决二者矛盾?中国古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设计出了解决方案-类推。在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况就说过-“有法者,依法行;无法者,以类举”。所谓“有法者,依法行”,即有法律规定的,就按照法律规定来处理;所谓“无法者,以类举”,即没有法律规定的,就按照类推的方法来处理。显然,“类推”和“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处理”是有所不同的。在“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处理”情况下,法律的规定与案件的事实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同一性。而在“类推”的情况下,法律的规定与案件的事实之间则不存在着这种逻辑上的同一性,而存在逻辑上的类似性。显然,同一性与类似性是有所不同的。通过类推使法律规定不仅适用于和法律规定之间具有同一性的案件事实,而扩大适用于和法律规定之间具有类似性的案件事实,从而扩大了法律适用的含括面。因此类推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法的有限性”和“情的无穷性”之间的矛盾。通过类推,使那些虽然在刑法中没有规定,但与刑法规定最相类似的危害社会行为能够按犯罪来处理。因此,类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法的有限性”和“情的无穷性”之间的矛盾,但能在相当程度上缓解“法的有限性”和“情的无穷性”之间的矛盾。
因此,在过去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古代封建刑法当中,始终采用类推的方法来定罪处刑。在封建刑法当中,有所谓“比附援引”,这种“比附援引”实际上就是一种类推。在中国古代“唐律”中,还规定了这样一个法律适用的原则,“入罪,举轻以明重,出罪,举重以明轻”。所谓“入罪,举轻以明重”,指一个行为在刑法中没有规定,要把它作为犯罪来处理,那么就可以采取“举轻明重”的方法。这里所谓“举轻明重”,指当一个比它更轻的行为在刑法中都规定为犯罪,这个行为比它重,当然更应该作为犯罪来处理,这就是所谓的“举轻明重”。所谓“出罪,举重以明轻”,指一个行为在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不是犯罪,要想不作为犯罪来处理,就可以采用“举重明轻”的方法。这里所谓“举重明轻”,是指一个重的行为在刑法中规定为不是犯罪,这个行为比它轻,当然更不应该作为犯罪来处理。通过这种“举轻明重”、“举重明轻”的方法,可以使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达到或者“入罪”、或者“出罪”的结果。当然,和我们讲的类推有关的,主要是“举轻明重”的问题。通过“举轻明重”,使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能够按照犯罪来处理。
为了说明“举轻明重”的问题,可以举一个例子。某地有一条交通规则-“禁止牛马通过”。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是骆驼通过了,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能否用“禁止牛马通过”的交通规则禁止骆驼通过,或者说骆驼通过是否违反了“禁止牛马通过”这一交通规则。对于这一问题,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第一种观点认为,交通规则是“禁止牛马通过”,骆驼既非牛、又非马,当然不在禁止之列;另一种观点认为,交通规则之所以禁止牛马通过,而不禁止鸡狗猪羊通过,是由于牛马的体积、重量都比较大,它们通过会扰乱交通秩序,而鸡狗猪羊这种小型动物,它们通过了,则不会扰乱交通秩序。但骆驼,无论从体重还是其他方面来说,都会超过牛马,它通过了,当然会扰乱交通秩序。既然牛马通过了要禁止,骆驼通过了当然要禁止。这两种答案它们的基本立场是不同的。前一种答案坚持的是形式合理性的基本立场,也就是说,一个行为能否为法律所禁止,就看法律的明文规定,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才予以禁止。这个法律规定的是“禁止牛马通过”,并未包括骆驼,不能用“禁止牛马通过”的规定来禁止骆驼。而后一种观点所坚持的是实质合理性观点,这种实质合理性主要是通过对这条交通规则的立法原意来加以分析,然后根据“举轻以明重”的逻辑方法推论出来。所以这两种观点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立场。
那么在这两种不同的立场中,我们到底如何选择?是选择形式合理性,还是选择实质合理性?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应当说,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对实质合理性的观点都是十分赞同的,并且往往按照实质合理性的观点来判断问题。比如说,公园里边有一个池塘,池塘里边养着鱼,公园管理人员立了一块“禁止垂钓”的警示牌,有一个人不是在钓鱼,而是在张网捕鱼,公园管理人员前来制止,面对公园管理人员,张网捕鱼者为自己的行为作了这样的辩解:警示牌上写的是“禁止垂钓”,但我并没有在这里钓鱼,而在这里捕鱼,捕鱼没有被禁止,也就是说不能根据“禁止垂钓”的规定来禁止我的张网捕鱼的行为。对他的这样一种辩解,我们任何一个具有正常理智的人都会作出这样一个判断:狡辩。我们都会赞同公园管理人员根据“禁止垂钓”的规定来禁止张网捕鱼行为。在我们这种判断的背后,实际上坚持的是实质合理性的立场,这是根据“举轻以民重”的逻辑思维方法得出的结论。池塘里面既然连垂钓都不允许,那么张网捕鱼更不允许。由此可见,实质合理性的思维方法在日常生活中是得到普遍认同的,人们都是按照实质合理性的思维方法来思考问题、判断问题。
不仅如此,这种建立在类推基础上的实质合理性的思维方法,在有关的法律修文中也是经常被采用的。比如说在民法中,在民事案件的审判中,就广泛采用了类推的方法,在拿破仑的民法典中,有这样一个规定,它认为,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官不得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拒绝受理民事案件,否则,这个法官构成犯罪。也就是说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官面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不能说该民事诉讼如何解决在法律上无明文规定,因此不能受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否则,就要构成犯罪。那么既然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民事纠纷,法官也必须受理,那么受理后如何进行审判?按照什么样的法律根据进行裁判?这里涉及到民法的基本原则。民法的基本原则是诚实信用,这个原则使民法典成为一个相对开放的规范性体系,它使得民法典具有空旷的结构。因此,诚实信用原则给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官自由裁量留下一个广阔的空间。因为诚实信用是整个民法典的法律精神,那么所有民事法律规范都体现了诚实信用原则。所以,在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按法律规定进行审判,实际上就是按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审判。那么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也可以从诚实信用这一民法基本原则中推论出一些具体的规则,适用于具体的民事案件。因此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官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具有创制法律的功能,一种造法的功能。这一点从我国最近几年民事审判的实践来看,表现得极为明显。比如在过去的民法中我们不承认精神损害赔偿,而认为人的精神,包括人格、名誉,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是无价的。因此,精神受的损害不能通过物质赔偿来加以弥补。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精神的价值愈加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精神损害应当受到物质赔偿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1997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第一例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原告人贾宫宇,是一个17岁的女中学生,她和家人到一家火锅店吃饭,由于卡式炉产品质量问题,发生了爆炸,造成了贾宫宇毁容的后果。海淀区法院在法官在审理时,不仅判处它所遭受的肉体损害获得赔偿,而且对她的精神损害赔偿要求也得到了支持。因此作出了全国首例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例。然后,全国各地法院也纷纷效仿,后来的司法解释,也确认了“精神损害也应当获得物质赔偿”这样一个原则。再后来,有关法律中也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从“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法律问题的解决来看,是一个从“个别判例—司法解释—法律”这样一个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在这一法律规定的形成中,法官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我们说在民事审判中,法官造法功能体现得十分明显。
此外,在近几年,随着网络的发展,在网络当中出现了大量网络的专利权、著作权、名誉损害的纠纷。这些纠纷出现以后,不可避免地要起诉到法院来,而法律总是滞后的,法律当中关于网络纠纷的案件没有明确做出法律规定。在此情况下,法官就不能说网络纠纷在法律中无明文规定而不予受理,这是不允许的。那么受理以后,在法律上无规定,只能按民法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然后比照有关法律规定作出一个适当的判决,这种判决逐渐积累经验,为以后的司法解释乃至民事立法提供一些素材。从这里可以看出,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基本原则,对于民法典来说具有开放的机能,它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提供了法律的根据。所以这种类推的方法在民事审判中是广为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