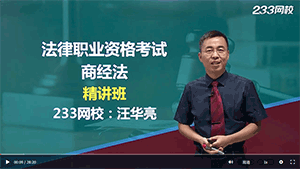二、传统犯罪客体理论存在着犯罪客体立法功能和司法功能的混同
刑事立法的理论是宏观的,刑事司法的实践是微观的;刑事立法的根据是抽象的,刑事司法的根据是具体的。在刑法领域中,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两者关系就如在建筑领域中设计师与施工者两者间的关系一样。在建筑领域中,一幢大楼如何选址、如何设计,其基础要求是什么,其结构要件是什么,一切都在设计师的视野和思考之中。建筑设计的每一步、建筑结构的每一处,都要求设计师具有充足的理论依据,都离不开设计师的精心论证。建筑设计方案已定,对于施工者而言,其任务就是严格按照图纸精心施工,进行一砖一瓦的堆砌,以实现建筑设计的既定要求。建筑设计的根据和理由已不是施工行为本身的内容。两者的性质和任务是十分明确,截然不同的。刑事立法犹如建筑设计,一种行为为什么被规定为犯罪,其根据和理由是什么,不能不作出说明。刑事司法犹如建筑施工,一种行为为什么被认定为犯罪,只需要说明已有的事实材料(包括主观罪过和客观行为)是否已符合刑法的实在规定。至于这种实在规定背后的根据和理由已用不着刑事司法工作者越俎代庖地再加以论证和说明。
然而在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中,由于存在着犯罪客体这一犯罪构成的要件,使得刑事立法的应有功能和刑事司法的应有功能被混为一谈。本来由刑事立法需要论证和说明一种行为为什么被规定为犯罪的根据,在刑事司法中又被不厌其烦由司法人员再三论证和说明。于是在大量的司法实践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在司法机关指控或确定一个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时,往往不是根据已有的行为事实,来分析认定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和客观行为是否符合了法律的规定,而是喜欢首先大谈特谈行为侵犯了某一种犯罪客体。不指出行为首先具有违法性,而说明行为首先具备了犯罪构成的客体要件,不过是主观先验的反映。在刑事立法过程中,一种行为具有了社会危害性,才被纳入刑事违法性的选择之中,这是行为为什么被规定为犯罪时的一种价值评价,它反映了犯罪设定过程中的立法功能。而在一定罪过支配下的危害行为已经具有了刑事违法性,具有刑事违法性的行为必定具有社会危害性,这是行为被认定为犯罪后的一种规范评价,它反映了犯罪认定过程中的司法功能。这样,以社会关系为内容的传统犯罪客体,可以成为刑事立法设立犯罪的根据,而不可能成为刑事司法认定犯罪的依据。但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把犯罪客体纳入到犯罪构成之中,并视为首要的要件。这就意味要求刑事司法在认定每一个犯罪时,必须首先认定行为是否侵犯了某一种犯罪客体。然而,没有行为首先具有的刑事违法性,又何来行为对犯罪客体的侵害?而要求刑事司法必须说明行为对某种社会关系具有社会危害性,才被认定为犯罪,事实上就是要求刑事司法必须站在刑事立法的立场上回答着这一问题。这样,在刑法上设罪的立法功能和定罪的司法功能就被简单地同一化了。
但是我们必须要指出,社会关系(实际上是社会利益)的确是刑事立法所要保护的对象。刑事立法设立每一个犯罪,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护某一个既存的社会利益,表明了刑事立法的某种价值取向。刑事立法设立某一种犯罪,它并不都以社会现实生活中已存在这种行为事实为前提,它只是预示性地向社会成员宣布刑法将禁止这种行为的实施。当社会生活中一旦出现这种行为,通过司法实践的严格依法认定与惩罚,实际上就已实现了刑事立法的保护目的。所以,刑事司法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认定某种行为是否符合刑法的规定,而无需回答行为为什么被规定为犯罪。行为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其社会危害性再大,也已在刑事立法的容忍范围之内,如卖淫、嫖娼、通奸、吸毒等等。行为已具有刑事违法性,哪怕是过失行为,仍然要依法惩处。因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当我们认定一个行为是否应当、为什么应当构成犯罪,其实一个很简单的理由,那就是行为符合了刑事违法性的规定。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试图通过犯罪客体揭示一种行为为什么构成犯罪,无非是要刑事司法转换为刑事立法重新论证犯罪的立法根据。这不但混淆了刑事立法者和刑事司法者不同的功能,而且也是司法成本浪费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代法制社会有一个明确而普遍的要求,即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相分离。刑事立法所要解决的是设立犯罪的根据和设定犯罪的要件,刑事司法所要解决的是认定犯罪的性质和印证犯罪的要件。而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把犯罪客体既看成是立罪的根据,又看成是定罪的根据。从表面上看,似乎瞻前顾后,面面俱到。但实际上恰恰把司法功能混同于立法功能,让其扮演着双重角色。但这种功能的混同已与现代法制要求相去甚远了。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所存在着的犯罪客体的立法功能与司法功能不分的现象,其深层的原因不但在于我们前面揭示的犯罪客体的政治功能与法律功能的混淆,而且还在于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确实存在着立法与司法一体化的现象。但是我们应当看到,随着依法治国的时期到来,让法律相对独立于政治,让司法绝对独立于立法,这已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一旦法律相对独立于政治,司法绝对独立于立法,那么,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所存在的弊端就会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这是因为传统的犯罪客体所要揭示的社会关系是一个一直处于发展、变化过程中的现象,于是一个行为对社会关系所发生的影响,完全可以随人们任意评价。这种任意的评价也许会带来法律的变更或修改,但我们仍无法否认,法律一经制定施行,就已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这种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表明在已然的刑法之中,它对违法犯罪设立的规格、标准是固定的、明确的、具体的。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我们用不着在犯罪规格之外的设立根据中寻找理由,也用不着在所谓的社会关系中理解犯罪的法律性质。以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为指导而设立的犯罪构成,有着明确的、具体的主客观要件的内容,符合者为犯罪,不合者为非罪。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把犯罪客体纳入到犯罪构成中,要么产生先验的作用,把某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任意夸大后,再印证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性。而这种先验性的作用,无疑会对任意出入人罪产生影响,要么在认定行为已经符合法律规定性之后,再引申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但此时已是犯罪认定后的规范评价,与犯罪认定的规格依据没有必然的联系。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试图通过以社会关系为内容的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来印证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不过是站在刑事立法的角度夸大它的刑事司法作用,成为尾大不掉的成份。长期以来,我们在很多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经常看到的某些“假大空”的现象,不能不说这是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在其中发挥着最大化的负面影响。
随着法制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入,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相分离,预示着传统犯罪客体理论的必然终结。即使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把“犯罪客体”定义为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也仅仅表明它是刑事立法设定某种犯罪的根据,仅仅具有立法的功能。当司法实践认定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其法律根据在于犯罪构成规格本身,而不是这种规格背后的设立依据时,“犯罪客体”已不可能再具有司法的功能了。当今天我们打开一部部自视为“权威”的刑法教科书时,看到每一个犯罪构成中无一例外地首先排列着犯罪客体这一要件,真不知这是从立法功能的角度提出的,还是从司法功能的角度设立的。而这种融立法功能与司法功能于一体的传统犯罪客体理论的继续存在,也正说明了我国刑法理论的幼稚和僵化。还需要指出一下,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和其他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在本质上都是危害社会、影响社会秩序的行为。只是由于不同的法律规定,而形成不同的违法性。不同的法律规定着不同的违法性,对立法者来说,都是为了保护既存的社会利益。保护既存的社会利益都体现着立法的应有功能。在犯罪构成中增加一个犯罪客体,以此在司法实践中体现它的定罪功能,势必意味着在其他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结构中也有着一个违法客体。然而,时至今日,其他违法行为结构中并没有存在过这样一个违法客体,这既没有影响其他法学理论的科学和完整性,也没有妨碍其他司法实践对违法行为认定的准确性。这种从比较研究中产生的启示既深刻又浅显地告诉我们,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也该退出刑法理论的舞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