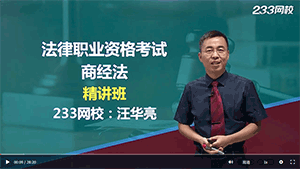三、传统犯罪客体理论存在着对犯罪客体研究角度和研究目的的混乱
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至今仍然顽固地存在于我们的刑法理论中,还有一个我们丝毫也不能忽视的原因,这就是在认识、研究和评价犯罪客体时,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的坚持者经常发生着研究角度的随意变换和研究目的不时转移,从而使传统的犯罪客体,以不变应万变地维持着其自身的生命力。
传统的犯罪客体一开始就是理论研究的产物,直到现在为止它还仍未被实在法所认可并加以明确规定。而一向被认为既具有法律属性,又具有理论属性的犯罪构成,由于容纳了犯罪客体这一要件,使得其自身的法律属性大打折扣。一定的刑法研究是和一定的刑法观联系在一起的。刑法观是关于刑法本质、刑法目的、刑法功能和刑法效果的总的观念。任何社会总是存在着多层的刑法观。在社会利益主体不同,各个集团、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个政党存在严重对立、激烈对抗的状态下,统治者的刑法观总是处于主导支配的地位。而在社会各利益主体处于相互容忍、相互协调、和平共处之时,刑法就成了社会各利益主体协调的产物,甚至是社会全体成员意志的结晶。此时,公平、平和、折衷的刑法观就应占据支配地位。回顾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的创立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创立者是在阶级斗争(有时是被夸大了)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站在政治需要的高度,首先以服务于立法目的,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对已有的实在法进行分析归纳后创造的。我国的犯罪客体理论是照搬前苏联的犯罪客体理论而形成的,两者一脉相承。在阶级斗争的时代背景下,站在政治的高度,服务于立法的目的,把犯罪客体视为统治阶级认可并要保护的社会关系(社会利益),以此说明犯罪的设立根据,这里研究者的研究角度与研究目的有它的同一性。然而当犯罪客体一纳进犯罪构成,成为其中的一个首要要件,此时研究者的研究角度与研究目的又已经开始转移到了司法的立场上了,是从定罪的角度来分析,研究犯罪客体,把它视为定罪的一个构成依据。于是,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的创立者和继承者、坚持者同时兼有立法活动发言人和司法活动发言人的双重身份,并根据需要不断地变换研究角度,以服务于不断发生转移的研究目的。当阶级对立、对抗的时代已经过去,现代法制时代已经到来,立法与司法已经分离,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仍然固守着旧有的战斗阵地,呈现着明显的“刻舟求剑”迹象。而伴随着这种研究角度和研究目的的混乱,犯罪客体中政治功能与法律功能的混淆,立法功能与司法的混同就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传统犯罪客体的坚持者一会儿站在政治的高度,从立法的角度,以权威的口吻阐述着一种行为为什么被规定为犯罪;一会儿又站在法律的阵地,从执法的角度,以虔诚的心态解释着一种行为为什么被认定为犯罪。犯罪客体就像万能良药一样,解决着立法与司法中的一切疑难杂症。(注:笔者在外出授课之时,不止一次地听到授课对象提起,他们在初学刑法之时被告知,只要掌握了犯罪客体理论,就等于掌握了刑法的精髓。)
其实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自身的定位是十分重要的。对一个事物、一种现象的研究,我们的研究目的应当是明确的,研究的立场应当是固定的,只是采用的研究方法可以是多样的。尽管有时为了获得对某一事物、某一现象的客观公正的认识,我们可以变换不同的角度进行多方面的观察,但是角度的变换仍须受研究目的的支配。不然,角度的变换却导致了研究目的转移,那么得出的结论就会与研究目的相去甚远。一辆汽车在大街上行驶,物理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为的是研究机械运动的规律,化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为的是研究汽油分子的散发,交通警察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为的是掌握交通规则的执行。把机械运动看成是化学现象,把汽油散发看成是交通现象,把交通规则看成是物理现象,其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只能是缘木求鱼,难成科学。然而在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中,研究者本来站在立法者的立场上,研究一种行为为什么要加以规定为犯罪,把保护某种社会利益作为自己的研究目的和刑事立法的目的。但是在其研究过程中,却又随意变换了研究角度,把对刑事立法根据的研究转移到刑事司法根据的研究,进而把刑法保护的客体直接纳入到犯罪构成要件中,视为刑事司法定罪的根据。这种研究角度的变换和研究目的转移,使研究者对犯罪客体的论述,连他们都无法说清楚自己到底是立法的解释者还是司法的诠释者。本来十分简单的一个行为为什么被立法规定为犯罪和一个行为为什么被司法认定为犯罪的道理,在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中被叙述得混乱不堪。为什么在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中会经常发生这种研究角度的变换和研究目的的转移,也许在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者看来,当他们站在立法者的立场提出以社会关系为内容的犯罪客体时,试图借助立法的权威性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权威性;当他们站在司法者的立场论证以社会关系为内容的犯罪客体时,又试图以司法的实践性来证明自己理论的实用性。但这种研究角度和研究目的的混乱,正像立法功能和司法功能的混同,是无法体现其科学价值的。
在涉及到传统犯罪客体理论研究角度和研究目的经常发生的混乱时,其研究的方法也值得我们思考。中西方文化在研究社会现象时,呈现出两种颇为不同的研究方法。西方文化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分析研究。分析成了西方法学文化研究的精髓。西方法学的很多成就,主要来源于此。即使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现象,撰写出不朽的巨著-《资本论》时,也是首先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商品-着手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恩格斯在研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也首先从对氏族社会的发展变迁的分析研究中,揭示国家产生的必然规律。而东方文化的研究方法往往侧重于归纳,表现为一种“寻亲和归元”(注:周汝昌:《思量中西文化》,载1999年5月30日《文汇报》第7版。)的方法,摒弃细琐零碎、分散支离的“取向”直奔归宿。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固然各有千秋,然而分析的方法使某种结论更具有坚实的基础却是不容置疑的。反思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理论的创立者和坚持者,并不是从分析研究着手,而是直接从先哲的皇皇著作中寻章摘句地寻找根据,从既定的、固定的概念出发加以演绎。而我国的传统犯罪客体理论更是不加思索地照搬抄袭前苏联的犯罪客体理论而出现并继续存在的。前苏联的犯罪客体理论一开始就是在“每一个犯罪行为,无论它表现为作为或不作为,永远是侵犯一定的客体的行为”、“任何一种侵害行为的客体,都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是社会主义刑法体系中的犯罪的客体”(注:[苏]特拉伊宁:《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01~102页。)的结论前提下展开的。为什么社会关系变成了犯罪客体,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论证犯罪行为直接指向社会关系这一客体,在前苏联的犯罪客体理论中,除了许多空洞的政治性论述之外,我们很难看到这一理论的坚实基础。而我国的传统犯罪客体理论只是通过简单的“寻宗和归元”,视前苏联的犯罪客体理论为经典,可谓以讹传讹,抽象有余,具体不足。以致于在利用这种犯罪客体理论解释犯罪时,在行为是否可以构成犯罪之前,经常不着边际地大谈特谈某种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并进行无限地抽象拔高,似乎不唯此不足以说明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当真正衡量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又只好用具体的犯罪对象来加以论证。即使在行为人发生认识错误,误将死尸认为活体,误将野兽认为是人而进行“杀害”时,仍然僵化地认为这里还是存在着一个“社会关系”,一个“人”的生命权,而看不到此时成立犯罪的根据在于行为人在一定罪过支配下的行为已符合了法律规定性。由此可见,传统犯罪客体理论赖于生存的简单的“寻宗和归元”式的演绎方法,多少反映着我国刑法学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僵化的思维定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法学幼稚和肤浅”的讥讽提供着实证材料。
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在我国刑法学中是根深蒂固的,对它的反思和清理,其任务是沉重的,其过程可能是漫长的,许多条条框框,包括许多“权威”的结论仍紧紧束缚着我们的思想。可喜的是,当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已经完全脱离了现实生活并已不适用于司法实践时,我们的司法实践对一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并进行惩罚,并不是按照着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进行操作的。罪刑法定的原则时时提醒着我们没有必要去理会这种犯罪客体理论对定罪的所谓重要意义,只需要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指导下的并以此为内容的犯罪构成加以印证即足矣。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不过是在行为认定犯罪之前或行为认定犯罪之后借机发挥一番罢了。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我国的刑法学理论正面临着体系的重构和内容的更新。当我们的刑法学理论要以科学的体系重现于世,当我们的刑法学理论要以科学的内容在更高层次上担负起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重任时,指出传统犯罪客体理论的诸多弊端,并最终结束它的历史命运,仍然是十分必要的,非常迫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