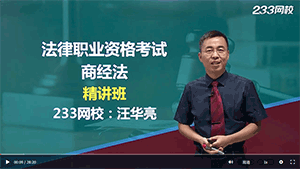三、关于“社会危害性”问题
犯罪的本质属性在于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犯罪概念中必须包含这一要素。对此,无论在刑法学领域还是犯罪学领域均无争议。显然,如果某一行为对社会没有严重危害,刑法就不会将其规定为犯罪并力图通过社会制裁体系中最严厉的手段-刑罚加以遏制;犯罪学也不会去探讨其存在的状态、原因和采取的预防措施。这样,这种行为就既不会成为刑法学上的犯罪,也不会成为犯罪学上的犯罪。但是,对于“社会危害性”这一犯罪最本质的特征,刑法学与犯罪学是否是在同一意义上理解的?对此,学界鲜有正面论述。笔者认为,回答应当是否定的。认识到这一基本点意义重大。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刑法学犯罪概念与犯罪学犯罪概念区别的实质,而且关系到科学的犯罪观主要应当在何种程度犯罪概念的基础之上建立。
在刑法学视野中,社会危害性,首先是基于立法的需要,即作为立法者回答“何种行为应当被判定为犯罪以及对所规定的犯罪应当如何处罚”这一问题的依据而提出的。但作为刑事立法依据的社会危害性,不仅在于其本身的客观性,而且也在于立法者对这种客观危害性的主观认定。换言之,“正是犯罪行为客观的社会危害性连同它的其他属性一起,才是承认这种行为是犯罪和应受刑事处罚的根据。”(注:[苏] b·h·库德里亚夫采夫主编:《犯罪的动机》,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9 页。)这里的“其他属性”,应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被赋予了鲜明的阶级内涵。按照马克思法学基本理论的观点,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刑法是由掌握国家政权的阶段即统治阶级根据自身的意志和利益需要而制定,并为其统治服务的。刑法的阶级本质决定了立法者在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将一定行为规定为犯罪时,不可能只从该行为对社会的客观危害角度去考虑,而必须同时充分顾及维护现行统治关系的需要,即必须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从阶级利益出发进行评价。在作为统治阶级代言人的立法者看来,应当在刑法上的被规定为犯罪的只是这样一些行为:一方面,这些行为对社会具有一定的客观危害性;另一方面,这些行为对统治阶级力图建立和维护的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社会秩序构成了现实的严重危害,也就是说,这种行为的侵犯性与主体意志(统治意志)具有明显的不相容性。刑法上的犯罪只能是二者结合的产物,并且在正常情况下,二者之间越接近,则行为被规定为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对其配置的刑罚也越重。这是古往今来创制法律的定式。刑法在规定犯罪方面遵从于社会危害的客观性,体现了犯罪的社会性,即犯罪其有对某一社会形态中的各阶层利益以及整体利益造成危害的事实特征。(注:参见杨春洗、杨敦先主编:《中国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这也是刑法得以实施的必要条件。如果将根本没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则刑法就会因缺乏最基本的社会基础而无法实施,立法创设罪名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而基于统治意志对社会危害性进行评价,则反映了刑法规定犯罪的政治趋向。如此,刑法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才能发挥作用。由于刑法是产生和存在于阶级社会中的,因此在规定犯罪的社会性与阶级性方面两者之间不可能完全吻合。前者始终会受后者制约。在专制政体或剥削制度下,所能看到的正是二者之间不可能完全吻合。前者始终会受后者制约。在专制政体或剥削制度下,刑法也是根据社会上各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有选择地宣布某种行为是犯罪的,(注:参见肖扬主编:《中国新刑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在规定犯罪方面也只能追求社会性需要与阶级性需要之间的最大限度的近似值,不仅不可能将客观上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都规定为刑法上的犯罪,而且也难以避免在特定条件下将不具有或只有较小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也视为刑法上的犯罪。这说明了“刑法上规定的行为有政治色彩,国家把某些行为定为犯罪的行为原本就具有政治色彩。”(注:[美]理查德·昆尼等:《新犯罪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其次,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具有主客观相统一的属性。刑法将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其目的在于通过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主要表现为刑罚处罚)以遏止这类行为的发生。而遏止的前提是:行为人具有辨别是非和控制自己行为的主观能力;否则,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就形同“对牛弹琴”,不仅难以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而且也背离了刑法保障人权的宗旨。因此,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社会危害性的内部结构是主客观的统一,即只有一定的人在罪过心理支配下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才可能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社会危害。(注: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这也正如日本学者所提出的那样,“作为刑法学对象的人在成为负担作为对犯罪行为进行法律非难的责任的主体时,同时也成为包含改善要素、赎罪要素的刑罚的主体。”(注:[日]大冢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如果离开了行为人的罪过心理,只着重于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则制定和适用刑法所追求的这种改善要素和赎罪要素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此,纵然行为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行为人并无罪过心理,则该行为就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危害行为,从而排除了其犯罪性。
因此,刑法上的社会危害性,并非本来意义的社会危害性,而只是客观分割性与统治意志不相容性的统一,是主观罪过和客观危害的统一。这决定了以刑法为研究对象的刑法学,只能戴着这层面纱去理解能表征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各种法律要素。然而,从犯罪学角度看,对社会危害性的这种理解是很不适宜的,与犯罪学的研究任务和存在价值也是不相容的。
在犯罪学视野中,某些行为之所以被称为(被视为)犯罪,不在于立法者的判定,而在于它对社会的客观侵犯属性。这种客观危害,尽管理论上可以有不同表述,但在笔者看来,就特定社会形态而言,其实就是对该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实际侵犯。这种危害既不因统治者的意志和利益而转移,也不因行为人有无主观罪过而发生变化。“蔑视社会秩序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犯罪。”(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16页。)这些至理名言无不揭示了犯罪的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的客观本质。犯罪学坚持从客观事实角度考察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以此确定自己的研究范围,是由其学科性质和所担负的特殊任务决定的。
首先,作为事实性学科,犯罪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什么行为应当在刑法上规定为犯罪以及如何对规定的犯罪进行刑罚处罚的问题,而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分析何种性质和表现形式的行为才应当被视为犯罪(相对于社会而言,即什么行为才应当是引起负责组织社会生活的政府及国际社会关注的犯罪)、这些行为的状态和形成原因如何,以直接寻求能有效预防这些行为的途径和对策。作为研究的逻辑出发点,犯罪学在定义犯罪时,必须考虑到所定义的犯罪具有真实性,考虑到被称之犯罪的行为应当具有在广泛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在不同社会制度下进行比较分析的客观属性。否则,犯罪学的研究视野就会局限于立法者预先划定的行为范围。如此,犯罪学研究也将只能戴着刑法这付“变色镜”去确定什么是犯罪。这对犯罪学来说,结果将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这不仅有可能导致把只为统治意志所不容但对社会并无多大危害甚至有利于社会的行为纳入自己所力图预防的行为系列之中,出现研究目标上的根本错误,而且也难以透过内容各异、形式纷繁复杂的法定犯罪现象,着眼于犯罪发生和发展的自然过程去准确揭示带有规律性的犯罪原因(尤其是最具普遍意义的犯罪的社会原因)。这样,犯罪学所担负的促成社会理性认识犯罪和预防犯罪的任务就无法实现,其自身的特殊存在价值也无从体现。因此,犯罪学为了解决自己范围内的问题,在理解犯罪的基本内涵-社会危害性时,既不能附加具有阶级偏见的价值判断,也不能去考虑造成社会危害的人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如何,而只能尽量从本来意义上去把握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范围和表现形式,将真正具有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正因如此,犯罪学对已为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能理所当然地予以认同(对犯罪学来说,其间存在着是否应当予以犯罪化的问题),而是坚持自己的衡量标准,一方面以审查的态度和报考的眼光看待刑法所规定的犯罪,另一方面又将那些不属于刑法规定之列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例如,在刑法中无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和儿童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是被排除了犯罪性的,但在犯罪学领域,却将其作为两类具有独立意义的犯罪进行研究。因为精神病人和儿童实施的反社会性行为与其他人实施反社会行为,都同样具有犯罪的同质性,因此,也必须进行预防,否则,犯罪学就不成其为犯罪学了。在这类问题上,犯罪学所遇到的唯一差别仅仅在于前者犯罪的原因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而在预防上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特别措施,但绝对不存在否认其犯罪属性从而不需要进行预防的理由。
其次,从犯罪学研究的初衷看,它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才产生的,而是基于刑法在犯罪控制方面的苍白无力状态,力图通过探讨人们为什么会实施侵犯以及如何有效控制和减少这些行为,以努力改善社会自身的生存条件。这样,犯罪学在探讨犯罪的社会原因时,自然就会从是否有利于预防和控制犯罪发生的角度,对体现统治意志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进行批判性评价,以期促进社会犯罪防范体制建立和完善。仅在这一点上,犯罪学上的犯罪概念不仅不能被动接受刑法(学)对社会危害性的规定(理解,)而且还要对其合理性和在犯罪控制方面的实际功能基于自己的经验性研究作出分析和评价。在确定自己研究的逻辑起点时,只尊重社会危害性的客观属性,也因此成为犯罪学研究的传统学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