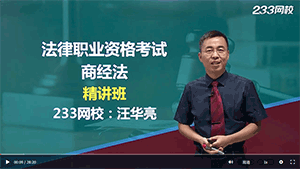长期以来,在我国的行政管理中,对私权往往持蔑视、排斥的态度,并不承认公实际是寓于私,公只是私中的共同部分。公权对私域的介入、干预也颇为随意、平常。其动机可能是善意,是充满“父爱”的,但其结果不仅使公民个人的权利利益处于较大的受侵害风险中,更无形中将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绝对、无条件地对立起来。似乎公权与私权在行政管理领域遭遇或碰撞时,唯一的所谓正确的方式,就是存公而弃私,甚至以公灭私。这其实是大可不必的,而且也极令人存疑的。哈耶克曾指出:区别一个自由的社会与不自由的社会的标准,乃是在自由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拥有一个明确区别于公共领域的确获承认的私域,而且在此一私域中,个人不能被政府或者他人差来差去。54事实上,自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从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兴起的“放松政府规则”改革运动中,就体现了政府权力从私人领域及事务中的撤离。
具体内容包括:将公共职能授予给私人部份和行政管制方式的变革。以市场自发调节的方式代替行政命令,使公私权力相互融合,或者私权力被运用于公益目的。……在行政机构进行自由裁量时,更多地依赖决策的谈判和磋商模式。……政府常被希望以一种与私人部门的模式一致的方式来行事…通过协商立法与执法等等。55由此可知,非强制行政行为也是顺乎时代发展的潮流的。它们的被采用,意味着在以往某些纯粹属于公共权力行使的领地,允许存在更多私人权利、愿望、意志、作用等成份,贯穿通行及协商、公平交易、平等往来、互惠互利等私法等活动原则。行政主体越来越多地适用私法原则及手段从事日常管理,是实现行政民主化,落实并保障公民各项基本权利的有效途径。行政相对方从“俯首听令”到“讨价还价”,如果单就某一行政合同的订立过程中看似乎不足道,但置于广阔的背景下观察,其又得以升华。即等于肯定并安排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之间,在旗鼓相当的基础上,通过合法合理的“对峙”与“冲撞”以寻找、划分行政权利行政相对方权利的“临界点”,以保持两者之间的相互平衡与制约。
而且非强制行政行为尚有为各类市场及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提供积极正确导向的功能。现代行政应是指导行政。行政即依法指导无损于规范。例如,行政指导通过帮助生产经营者消除盲目增强自觉性,避免错过竞争中的取胜良机;利用行政合同具有培育行政相对方自主、奋斗精神,促使其树立并承诺、守信用的观念,采取行政奖励,以树正气、弘扬美德、扬善抑恶,净化环境,行政调解其实也是一种遵纪守法、道德品质教育。这些从根本上说,均能进一步加强、坚固行政法律贯彻的实施的社会基础。
以行政指导为代表的各种非强制行政行为的应运而生并取代一部分强制行政行为是历史的必然。这种必然的取代源于市场经济,又反过来服务并推动市场经济,推动并实现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型。
(三)改变政府形象,改善执法环境,降低执法成本
勿庸讳言,在官本位、权力至上观念,年深日久的我国,现代行政法本应具有之协商、契约、合意之精神内涵,管理即是服务的思维观念,不易被接受更难于获弘扬。这在行政管理中的体现为,亲厚强制禁令,依赖惩罚制裁,对此类行为在行政立法中不厌其繁的规定和在行政执法中漫无节制的应用。而非强制行政行为无论从性质还是内容方面,均属于正面指导、扶持帮助、激励推动性的。这些行政行为的“溶入”,将有利于我国行政法做为“良法”之诸项品格与气质的树立与发挥,提高政府立法与执法的品位。再有,时下我国行政法在分配、配置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方面,不可否认的存在着某种失衡现象。即是说,在量与质方面均优厚前者而怠慢后者,这明显的有损公平、合理。改变这种情形的办法之一,在于扩充、强化后者。使之达到与前者大致的均衡、对等。56以行政指导为代表的非强制行政行为的设立与采用,在弱化行政权力强制性的同时,又增加了行政相对方权利的强度、力度。它意味着行政相对方更多的享有了拒绝权、参与决定权、主动要求权、分享荣誉和信息等社会资源权这些从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调解、行政资助、行政信息公开等行为均能得见一斑,可以肯定,非强制行政行为在行政管理领域的倡行其道之日,就是行政法“管理工具”的形象彻底改变之时。
寓管理于帮助、给付、授益之中,立足宽容、理解、信任,通过引导、沟通、协商,运用激励机制来调动人们主动、自愿地服从行政管理,是非强制行政行为的高明、独到之处。众所周知,近年来,在行政管理领域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之间的矛盾与纠纷层出不穷,某些本来可以避免的依旧产生、爆发甚至激化。正常的行政执法活动往往“好心不得好报”,非但不被当事人理解,旁观者亦有啧啧之声。原因之一便是善意的行政目的与生硬的行政手段之间达不到和谐统一。我们以为,为顺利实行行政管理,运用某些命令、强制手段固然必不可少,但客观的分析,由于其主观决断性强,追求显效,方式较简单粗暴,若使之成为独一无二的行政行为方式,势必引起行政摩擦的加剧,造成不必要的矛盾与对抗,且容易助长行政武断专横。相反,非强制行政行为则不然,它更容易使行政相对方感知、领受到法律对其自身的关怀、保障,排除对法律的异己感,代之以信赖和主动自觉遵守。由于非强制行政行为温和、具有弹性,实施中缓冲妥协余地大,可以削弱、抵消一般权力所固有的伤害力,降低行政过强的成本代价,诸如减少抗争,降低内耗,息事宁人,以防止行政权对行政相对方权利的侵害和自由的过分限制。
况且事实证明,在行政管理领域,以行政相对方对行政法规范的不合作、拒绝乃至不守法为假设,并试图通过施加某种威慑、压力乃至惩罚加以治服。这种怀疑加不信任仅仅针对少数人时是行得通的。现代行政法毕竟不再是专用来维持秩序与治安的规则。大面积的提供公共福利、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执行行政目的,早以使行政行为的成立与生效,不必以“强制实施”为必要条件了。显而易见,帮助人们满足各种利益需要的行政指导,体现契约、协作的行政合同,扶贫救困的行政资助,息事宁人的行政调解,包括交通、消防、安全生产法规,均可获得行政相对方的主动服从乃至积极合作。就大多数而言,对他们作出对日常行政管理行为的服从推定理所当然。
四、依法规范:非强制行政行为的法治化
(一)非强制行政行为法治化的必要性
由于非强制行政行为不象强制行政行为那样对行政相对方的利益产生直接、即时的影响,容易失去必要的监督和制约,且行政主体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治的实质是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的一整套规则。在法治社会不能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将非强制行政行为纳入行政法调整、规范的范围,是需要且必须的。理由如下:
1、这类行为对行政相对方的权利(益)、义务能产生间接的、事实上的不利影响。例如:对于不服从行政指导者,管理手段众多的行政机关可调用诸如加重税赋、不予免除义务,拒绝批准申请或给予优惠、乃至公布不服从行政指导者的姓名等其他行政手段,加以不“显山露水”的“整治”;生产经营等行政误导更可能给生产、经营者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行政调解属于行政机关插手公民法人之间,调停权利与权利间的相互冲突,若其自身行为不慎,也容易侵犯权利;不公正的行政奖励,不啻意味着限制、取消了某些具备资格的人们获得社会荣誉资源的权利;行政信息服务的“不作为”,将会置行政相对人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参与市场竞争、抵御行政违法侵犯等过程中的不利境地。
2、实施非强制行政行为,也会产生行政主体违法、侵权或者失职的问题。具体体现:其一、变非强制行为或强制行为。如,通过逼迫行政相对方服从行政指导或行政调解,强迫当事人接受霸王合同。其二,行为不规范,如:行政合同过程中,随机性的随意瞎指挥、滥干预。行政调解中,不分是非乱合稀泥。其三,不公平、公正、公开。如:行政奖励中,为善不奖。行政调解中,偏听偏信偏袒。缔结行政合同时滥用特权,无正当理由变更、解除行政合同且不予合理补偿等。其四,懈怠行政职责。如不及时提供行政指导,不适时公开行政信息,在行政合同实施履行中放弃行政监督,对所需人群危难不助贫弱不恤等。其五,以权谋私,例如行政奖励中搞收费,行政合同中进行虚假招标,在行政指导、行政信息公开时实施所谓有偿服务。其六,滥用职权或侵权。如:强迫相对方接受行政指导,实施行政误导,在颁布行政奖励中搞私相授受或挟怨排挤依法应获奖者。
3、无法避免行政相对方滥用权利的情形。例如:弄虚作假而骗取行政奖励、争取行政资助或行政奖励过程中搞比朋为奸;行政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偷工减料;滥用行政机关名义缔结行政合同、颁布奖励、发布信息等。
(二)非强制行政行为法治化的若干构想
长期以来,我国有关非强制行政行为的立法基本属于空白地带。国外有关这方面的立法亦不完备。只有少数国家,例如《日本行政程序法》(1993年)、《韩国行政程序法》(1996年)对行政指导作了专章规定,非强制行政行为的纳入行政法治化轨道将是一项长期、复杂、探索性但也颇具创造性的工作。我们仅在此作初步的设计构想:
1、行政行为理论应进一步渗透“平衡论”。平衡论要求行政法平衡地配置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的权利。57而欲在行政行为中寻求并锁定最佳的平衡状态,则须考虑某些使行政主体由发号施令者变平等的协商者的行政法律制度上的新设置。有人将之称为制度性的妥协。“所谓制度性妥协是指在体制内自觉地设置对立面或允许矛盾的存在,把对抗性要素因势利导纳入体制内部,使之成为促进新陈代谢的建设性力量。……当事人的不同权利主张在相互砥砺碰撞中达到一种法律关系的反思性平衡,找出一种对当事人各方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和判断……这正是现代民主的真谛。”58最体现权力与权利“平衡”的价值取向的行政行为,应当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双方平等交涉、谈判、协商乃至必要的让步的结果,而不是行政主体单方情愿一锤定音的产物。日本的行政对话制度、美国的制定行政规章的事先向利害关系人通告并协商、重大行政决定作出之前的听证制度等,都堪称对淡化行政强制性而增加其行政民主、科学化的有效制度和程序。其意义亦更深远。恰如查尔斯。泰勒所言“一个民主政府在进行决策之前与各社团进行商讨,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只是为了选定最受欢迎的政策,也是为了缓和与那些受损失者之间的磨擦,因为这些受损者至少会认为他们的意见曾被且将会再被政府听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