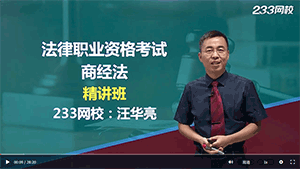非强制行政行为——现代行政法学的新范畴
作者:吉林大学法学院·崔卓兰 蔡立东
传统行政法学历来强调行政行为的强制性,将其视为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并认定强制性为一般行政行为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这一似乎天经地义的诠释,现已因无法回应实践的挑战而愈发陷入窘境。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熟,政府行使职能的方式不断发生变化,法制的规模和功能不断扩张,即:越来越多地采用带有契约、指导、协商、鼓励、帮助等具有私法性质的柔性手段来服务公众、管理社会。有目共睹的事实是: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奖励、行政调解、行政资助、行政信息服务得到广泛应用,并颇受青睐。继续置这一类非强制行政行为1于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之外诚属不智,行政法学研究应尽速对非强制行政行为倾以关注。本文旨在探讨非强制行政行为的性质、特征等,分析其根由及趋势,将这一新的理论范畴导入行政法学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非强制行政行为的确立
在我们看来,非强制行政行为主要包括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奖励、行政调解、行政资助、行政信息服务等不具有强制性的行政行为。对于上述行为的性质,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有学者明确肯定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奖励这三种行为是行政行为,在著作中将它们纳入行政行为范畴。但没有提及和置评同类的行政调解、行政资助、行政信息服务。2还有学者仅将行政指导、行政合同列入行政法学教科书体系,而忽视了行政奖励、行政调解、行政资助、行政信息服务的客观存在。3也有学者在行政行为一章中列举了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奖励、行政资助。行政调解、行政信息服务则成为行政行为家族的“弃儿”。4另有学者提出,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调解在本质上不属于行政行为,只是一种在主体、内容或形式上“与行政相关”的行为,可是不否认行政奖励、行政资助属于行政行为。5
分析学术界针对这类行为进行逐个研究的现状,可以得见,行政指导是行政行为得到普遍认同。而行政信息服务行为至今尚乏人问津。关于行政合同的性质问题,即其是否属于行政行为则是聚讼焦点,持肯定说者有之。持否定说者,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将之认定为“行政与合同两方面性质的综合”。6进而又引伸出其具有行政行为与民事行为的双重性质。另一种是将行政合同基本等同于民事合同,并将其置于民法原则与规则的调整、规范之下,强调对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行为中的行政特权不予肯定和支持。我国1988年颁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采纳吸收了此观点,该法第十八条没留余地的规定“承包经营合同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者解除。”
我们认为,行政指导等非强制行政行为虽不具有强制性,但不能因此否定其行政性质。因为行政主体实施的这些行为具备行政行为的基本要件:
首先,这些行为围绕并旨在实现一定的行政管理目标。如:为消除盲目生产经营或消费开展行政指导;基于完成公共工程建设需要而订立行政合同;旨在减少纠纷、稳定秩序而进行行政调解;意欲促进社会文明进步颁发行政奖励;为保证公民最低生活标准、消除社会贫困实施行政资助;为提高行政管理民主化程度、保障公民权利、防止行政腐败,而公布行政信息报考、提供行政信息服务等。
其次,这些行为以相应的行政职权为背景和基础。行政指导的发出;签订行政合同的动议;行政奖励范围标准的确立、审查批准以及奖励颁发;行政调解的主持;行政资助的提供;及以官方名义发布信息的资格等无不以行政主体享有相应的行政职权为前提条件。
第三,因这些行为而在主体间成立的法律关系与典型的行政法律关系具有同构化,可以而且必须纳入行政法律关系范畴,由行政法律关系的规则予以有效调整。具体体现为,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之间因非强制行政行为而形成的法律关系中,两者仍分别处于管理者和管理对象的身份、地位,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依旧不完全对等,行政相对方依然没有摆脱其相对于行政主体的弱势地位,需要得到处于弱势地位者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应该得到的照顾。具体体现在,行政相对方只能永远属于行政指导、行政奖励、行政调解、行政资助、行政信息服务的受领者。至于行政合同行为与民事合同行为相比较,双方在订立和履行合同过程中,后者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配置几乎完全对等,这是前者所明显无法达到,也是不应达到的。因此,现行的行政行为理论完全可以包容非强制行政行为。
第四,对这些行为的事后救济,多数亦须通过行政诉讼渠道,也从一个角度证明了行政指导等行为的行政行为性,因为通常只有行政行为引起的纠纷才能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事实上,正是基于对这些不以强制性为要素之行为的行政行为性的认同,各国行政立法多将由这类行为引发的行政相对方与行政主体之间的纠纷纳入行政诉讼范畴。如对于行政合同纠纷、符合条件而未取得行政资助的纠纷,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如德国、日本、葡萄牙等,已经相继以法规定了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在美国,根据其《情报自由法》等法律规定,公民依法要求政府公开有关行政报考遭到拒绝的,属于司法审查范围之列。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芬兰的《行政文书公开法》、法国的《行政文书公开法》、加拿大的《情报公开法》、澳大利亚的《情报自由法》等,关于行政指导,根据德国法律规定,行政相对方可以就要求给予或停止行政指导起行政诉讼。7行政指导制度发达的日本,尽管目前不能提起抗告诉讼(即行政诉讼),只允许声明不服,8但学术界反对之声愈渐强烈,亦存在改弦易张的可能。9行政调解尽管不属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其有时却做为行政裁决的前置程序,因而无法与行政诉讼割断其最终的联结。这些立法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利用行政诉讼独特的程序设置,如举证责任承担,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行政相对方给予民事诉讼无法提供的周到保护。另一方面也印证了将此类行为纳入行政行为范畴是可行的,不致导致行政行为理论的崩溃。
行政指导等不以强制性为要素的行政行为的客观存在,已经进入了一些学者的视野,国外许多行政法学家不否认这类行为的行政行为性,并试图对其进行理论诠释,以应对这类行政行为的客观存在对行政法理论的挑战,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两种观点:
其一为“非权力行为”说。日本的行政法学家室井力即持此说。他明确指出行政指导、行政合同乃至行政计划属于非权力行为。10我们认为,以“非权力行为”概括行政指导等不以强制性为要素的行政行为失之准确,没有把握住该类行为区别于强制性行政行为的特殊规定性,甚至可能引起行政行为理论的混乱。因为以行政权为基础、背景乃至后遁,是一切行政行为的本质属性。如果排除了权力因素,行政行为也就不成其为行政行为,而与一般民事行为无异了。行政行为尽管在方式上存在强制与非强制之分,但这不意味着在性质上有权力与非权力之别。行政处罚等强制行政行为须由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科处,行政指导等非强制行政行为也同样不允许由享有相应职权以外的主体,例如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实施便是明证。
对此杨海坤教授指出:行政行为既然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行为,那么它必定是一种权力行为。故不可将行政行为再分为“权力行为”和“非权力行为”。不过,权力行为可以分为“强权力行为”和“弱权力行为”。 11这种观点在肯定行政行为的行政权要素的前提下,清醒地认识到权力因素在不同的行政行为中有程度上的分别,可谓颇有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