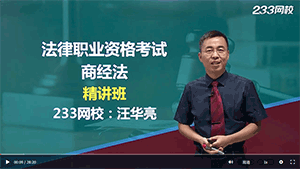(二)恢复利益的可能性
1.死刑是“刑罚”的一个形态。刑法第9条规定的“刑的种类”,虽说作为主刑至少每个种类具有“不同的性质”,但也必须同时在“统一性的原理”之下是可能说明的。因此,由于刑罚的“恢复侵害利益的可能性”的问题,也必须在与其他刑罚之间的对比上研讨死刑。
当作此研讨之际,关于“生命刑”和“自由刑”、“财产刑”之间的比较,由于刑罚被夺的“利益”上的“价值”(要保护性)有轻重,这一点必须当成理所当然的前提。“生命”优越于“自由和财产”,所以适应它而要求“罪刑之均衡”这点不论从报应和预防的任何一个观点上都能被肯定。因此,在这里对死刑强调(注:例如,正木,前列注(37)7页认为“生命的情况比监狱刑的情况也好,比财产刑的情况也好,要发生不成比较的尊贵物质的剥夺,在无可奈何的一点上与其他情况不同。”再有,宫泽浩一译, 阿尔徒尔·考夫曼《关于死刑》法曹时报1卷7号(1965)1024页认为:“其他的刑罚至少能够恢复到某种程度,与之相反死刑是完全不能恢复的。”进而,宫泽,前列注(37)88页,批判植松博士的见解而认为:“死去和活着,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阶段似的,但实际上它们两者之间有一个搭不起桥梁的鸿沟。活着的人可以诉说没有事实根据,然而死去的人却不能说自己。”另外,也参照前注(40)的迁本教授的见解。)“生命的价值”的“始源性、包括性”这样的特殊性,尽管这一点作为它本身来说是正当的,但因为它是利益剥夺之差异,也就是“生命的绝对性”的问题,所以在本研讨中不得不舍弃。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该问题是围绕“个人之尊严”的固有的论点,关于它本身,在另外的研讨(续稿Ⅲ一)成为正式的需要之故。这样,首先把考察的对象限定于“由刑罚被剥夺的利益”的“恢复不可能性”予以论述,这作为“问题的限定”并非不妥,作为研讨的方法(“讲坛”)是能够容许的。
2.且说,被剥夺的利益的“恢复不可能性”在生命刑上虽然是最大而显著的,但如果把其差异当作别论,于其本质上在自由刑和财产刑方面也同样不能否定。假定是这样的话,关于这个问题,死刑和其他的刑罚双方本质上没有差异,所以应该关联“死刑”存废的论点就不能产生了。
如果从“个人的尊严”出发,“生命”和“自由、财产”两者是相关性质的乃至补充性质的价值。“生命”是“自由”的才具有意义,利用“财产”得到维持。没有“财产”(衣食住)的“生命”贫穷脆弱,没有“自由”的“生命”像不会动的石头,不过是接近于有机体。相反地“自由和财产”对于死者也是无缘的,以“生命”作为不可缺少的前提才值得保护。
“生命”在时间空间上以有限的“一次性”作为其宿命,所以“自由和财产”是在每一个时间和场所维持和充实生命中不可缺少的。因此,不论是充满希望的青春时期也好,临近死期的病人的短暂时间也好,在该时间被剥夺的“自由和财产”也基本是不能恢复的。它并不是依存于期间之长短,效用之大小的。譬如,即使是仅仅一天的拘禁,和他在这时约会见面的人已去旅行,等于是今生永远不能再会了。就是剥夺财产也能产生同样的不能恢复,这是很明白的。就是说,“自由、财产”的剥夺也是以“生命在时间空间方面存在的一次性”为其前提的,所以,在此限度内完全是不能恢复的(注:关于这一点,植松前列注(38) 345页~346页上,正当地论述说:“说起来,人生是不可逆转的。 某一期间自由被束缚这一事实,也决恢复不了。进而是,此后一生的经历不得不改变将来的情况也不少见。在此意义上,自由刑的误判也不能恢复是很清楚的。即使是轻度的财产刑,到其被证明不实为止,不仅身分受限制,在社会性普遍信用上也受到重大影响,在不同情况下,会变成终于不能恢复的结局。只是,死刑是比财产刑,再是比自由刑是剥夺更为重大法益的行为,如果有了误判,则其结果是与之相应地重大的。因此,科处死刑必须要比科处其他刑罚更为慎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说成唯独死刑的误判,尤其是不能恢复似的说法,这不妥当。”)。
这样,“恢复现状(现时的)之不可能性”对于所有的刑罚是共同的,在生命刑和自由刑、财产刑双方上只能看出相对性的差异。因此,如果从“不能恢复剥夺利益的现状”来看,在所有的刑罚上,不能不产生“出于误判的弊端”。在这个意义上,在和误判之可能性的关系上,没有理由仅仅区分开“死刑”。
3.对于这样的结论,将会出现下面这样的反论乃至疑问。
自由刑的情形之下,第一,如果是其执行终结前的话,由于释放,能够回避“超过此刑”的自由剥夺。第二,如果认为财产不外乎是“被压缩的自由”,把该自由换算成财产,而“事后的补填”将和剥夺财产的情形一样是可能的。与此相反,生命刑的情况是,任何救济都是不可能的。对于被杀的被害人来说,就连事后的损害补偿都不可能,在这里,死刑的问题是明白的。
尽管如此,这些反论并不是决定性的内容。第一的救济可能性的差异,由来于死刑和其他刑罚之间的本质性差异。也就是,自由刑和财产刑上损害是部分性质的,在数量性质上能够计算,与之相反,生命刑却并非如此。这一点也连系到第二的事后补偿的差异。可是,这个差异,只不过是从“生命的尊严”这一个后面应该研讨的问题里派出生来的特殊性而已。再有,无期徒刑和长期的自由刑的情况下,其执行终结后的“事后补填”未必是奏效的,它和死刑之间的差异再次相对化起来(例如,服刑人在释放后就死去之类的情况。)不论怎么讲,事后性的补填,并不是纯粹的现状恢复,只不过是其代替手段。
从结论来说,不论是剥夺利益的“不能恢复现状”也好,“不能事后补偿”也好,都不仅仅是服刑人特有的问题,也是被害人的共同问题。因此,如果从“报应刑论”的立场来看,只是行为人和被害人同样应该蒙受剥夺利益而已。因此,这个论点本身,只有在把“回避误判之不可能性”作为其前提,对无辜执行死刑才具有意义。于是,必须把研讨转移到下面的“误判”的论点。
(三)回避误判的可能性
1.首先应把由于刑罚的“不能恢复剥夺利益的现状”作为前提,研讨“不能回避误判”的问题。在保留死刑论的立场上,由于认为不能恢复剥夺利益的现状是所有的刑罚上相对共同的,所以即使它和“不能回避误判”结合起来,也并非是死刑特有的问题(注:前注(38)、(42)中所列学说。另外,高濑畅彦《围绕死刑的法制(28)-死刑存废论会有结果吗?》搜查研究32卷(1983)11号80页认为:作为“制度论”的“误判”正是由于“法院的专权”被决定的,而并不是“客观性的事实认识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已经允许从死刑存废论的对象里取出。就是说,回避误判,只是作为刑事程序的一般性问题论述就足够了,关于死刑充其量只不过是把回避误判的刑事程序应相对地加以强化而已。
与此相反,废除死刑论的立场则是,应当认为不能救济恢复剥夺生命是死刑绝对固有的性质,“不能回避误判”对于审判和刑罚作为一般性的问题是不能容许的(注:参照前注(31)、(37)、(40)、(41)所列的学说。尤其是考夫曼,前列注(41)1031页认为:“尽管提出误判是罕见的但情况也好转不了。1000例,10000例当中, 只有一个人连罪也没有却被死刑执行官之手杀掉了,尽管如此,废除死刑也有充分的理由。”但,重要的是,这将是与其说回避误判之不能,勿宁说“个人的生命”连必要性都没有却被剥夺这是个更为根本性的“生命刑”的问题。)。总之,和自由、财产不同,只有剥夺生命是决不许误判的。
就是在这里两种论调也配合不起来,其对立的原因也未必就存在于“不能回避误判”其本身。其对立的原因在于:把“生命”与其他法益区别开来,是否承认构成生命前提的作为始源性的包括性的利益(注:参照前注(41)所列学说。)。尽管由于误判,不能回避自由、财产是不得已的,但构成其前提的不能回避生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是否应该这样考虑,形成了围绕死刑存废的对立。
2.由于误判,以执行死刑判决而被剥夺的生命,事后不能恢复救济。可是,就在考虑生命的价值是绝对的情况下,它可以成为废除死刑的绝对根据吗?关于这一点,站在保留死刑论立场上的竹田直平博士也展开了如下有力的异论:
“为了避开误判的危险,不言而喻讲求所有合理方法是必要的,但如把它作为理由要求立法中废除死刑,应该说与因为频频发生交通事故而为了避免这种危险,主张全面禁止火车汽车飞机等近代交通工具同样地,不,比它更加不妥当。(注:竹田直平《死刑(第32条)》日本刑法学会,修正准备草案,刑法杂志11卷2号(1961)116页~117页。 )”
总之,所有的人类活动都伴随不可避免的事故死亡(剥夺生命的过程),所以,其中仅是死刑把过失的危险作为理由而应该废除,这不成立。
针对这一论点,三原宪三教授说道:“只要是保留论者也说到的回避‘误判的可能’是不可能的,死刑将应该废除”,同时对于竹田博士的见解作出批判如下:
“认为是少有的误判从龟田案件开始,连着发生了三起。论者们主张说现代犯罪的证明方法逐渐地合理化、科学化了,但是不是在刑事司法的结构上有产生误判的土壤呢?(注:三原,前列注⑤168页、169页。)”
这位三原教授的批判是关于回避误判之不可能性其本身的内容,即使说其内容是妥当的,但假定基本没有对应于前述竹田博士主张的话,还不能成为针对它的反论。而且,在刑事司法上有“产生误判的土壤”的话,纠正它才是先决问题,而它也不是仅仅关联死刑的问题。岂但如此,对于三原教授的那种见解,渥美东洋教授的下述指摘,作为反论是重要的。
“确实,按说是期望十分慎重而作出判决的死刑案件,被认为是误判,这点会在误判死刑上成为根据吧。然而,在日本,已确定的死刑案件,长久不执行死刑,因此留下了重审机会,法律的实际运用受到注意的事例不少。这和镇压反体制者那样的国家,以及推迟执行已确定的死刑的各国不同,在日本,在命令执行死刑的法务大臣为首长的法务省里,实际上,关于确定死刑判决的问题重点,进行慎重研究的例行实务已经固定下来,这却出人意料地为人所不知。刑事诉讼法第47条第2 款虽明文规定在死刑确定后六个月以内法务大臣应该发出执行命令,但考虑到重审和非常上诉,对于法的”平衡“的要求,有请求重审、提出非常上诉,请求恩赦,到这些程序终结为止,还规定从这”六个月“期间里减掉。再有,在多数情况下,其犯人的共同被告人刑罚被确定之前的期限,也定为不计入这”六个月“的期限之内。”“留给上面谈到的法务省和检察官的死刑确定后的程序方针策略,确实一直回避了由于误判的死刑执行(注:渥美东洋《想一想我国的死刑制度》法律论坛43卷8 号(1990)27页~28页。另外,参照同《日本现行的死刑制度应该被废除吗?》刑法杂志35卷1号(1995)108页。)。”
据这个意思来看,可以看出确定死刑案件的重审无罪的连续出现,是防止由于误判执行死刑的刑事诉讼的规定和运用有效地发挥作用的结果。当然,这件事情,不是可以忽视误判造成的死刑由于原被告人等关系人难以描述的努力才好不容易得以避开了的事实(注:龟田荣《死刑制度之存废》龙谷法学28卷1号(1995)89—99页参照。)。再说, 也并不意味着误判死刑是经常可以避开的事情。
3.误判,不限于和死刑之间的关系,必须避开。可是,由于生命的份量,特别应该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回避误判的死刑,考虑设计出更能极限化的程序和运用。
尽管如此,社会的所有制度不可能是完善的,不能回避其过失这点也并不是就应该成为废除、禁止该制度、该行为的理由。扩大行动自由也好,充实防止犯罪制度也好,由于其活动领域的扩充,必然伴随扩大基于事故、过失的死伤。在这个意义上,在这里也将能够承认“被容许的危险”的法理。(注:参照长井圆,交通刑法和过失主犯论(1995)153页、175页。)(注:参照霍歇·约恩帕尔特《现在正在废除之中的死刑制度应该废除吗?》上智法学论集25卷1号(1981)21页。 )伴随新技术的一般性危险(risk),同时也扩大了自由而提高了生命的质量,在维持生命和健康方面也起着作用。现在正在努力整顿和改善能够防止其一般性以及具体危险的各式各样技术、程序、法规,并克服其弊害。这样也不能把由于发生过失的死伤为理由,就断定应该废除该制度整体。这一点,也将适合于刑事审判和死刑制度。
然而,如果认为“被容许的危险的法理”是一种“利益衡量”的法理,对于一定制度、行为的正当化、合法化来说,“利害得失”就是决定性的。前述的由于回避误判的死刑而扩充程序,也收敛于这个“利益衡量”的问题。死刑很容易被认为执行费用很少就可以解决问题,但为了避免由于过失的丧失生命应该最大的限度地重复慎重的刑事程序,所以就是限于为此的费用,也变成巨大数额。因为要剥夺最应该尊重的“生命”而以庞大的司法费用支持“死刑”这种“双重牺牲”果真能符合“利益衡量”吗?
进而,在把“过失死亡”和“故意杀死”两者同样看待时,会对把交通事故死亡和误判死刑两者等同视之而容忍的见解产生批判。对此也可以反论,驾驶也好审判也好都是故意作出,事故也好误判也好都是以过失乃至不可抗拒力量作出,作为制度整体来说是起因于“不能回避的过失”而招致死亡,在这点上是一样的。可是,死刑是所谓“计划性杀人”,和驾驶行为根本不同。因此,就是在这里,同“被容许的危险的法理”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它并不是危险行为究竟是故意还是过失的哪一个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能够回避其危险(risk)的“代替手段”。唯有它被否定的情况之下,作为“被容许的危险”,一定的制度、行为才能合法化。在死刑上缺乏其应该达到完成的效用(制止犯罪),如果以其他的刑罚手段也能达到完成目的的话,由于缺乏其“必要性”,死刑将不能作为“被容许的危险”而违法阻挡。
不论怎么讲,这样的归结,因为死刑是剥夺生命,是从不能回避“个人的尊严”问题产生的问题,而并不是从误判不能回避产生的。假定“不能回避误判”它本身是问题的话,则不限于死刑,就是其他刑罚,也是产生“由于误判侵害个人尊严”的问题的。因此,“以误判为理由的废除死刑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仍不能说是妥当的。